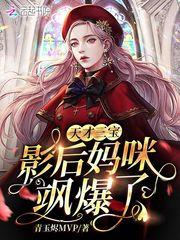笔趣阁>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480章 这是当初绑匪的全部证词(第1页)
第1480章 这是当初绑匪的全部证词(第1页)
商景予在酒店睡得。
她一晚上都没睡好。
做了一晚上梦。
各种人,各种事,都在脑海中挨个的浮现出来。
一大早。
霍长亭敲门,带着早餐赶到。
两人目光对上。
商景予说道,“进来吧。”
霍长亭什么都没说,“你先把早饭吃了,爷爷让全家人都回去一趟。”
商景予脚步一顿。
慢慢点点头。
若是老爷子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责备她……
商景予深吸一口气。
不管了。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填饱肚子,才是正事。
她洗漱完。
霍长亭已经将早餐热好,。。。。。。
地下室的空气潮湿而静谧,尘埃在斜射进来的阳光中缓缓漂浮,像是一场无声的雪。那行字依旧停留在屏幕上,墨黑底色衬着柔和的白光,仿佛不是数据生成的文字,而是从灵魂深处一笔一划刻出来的告白。
林知遥站在原地,指尖微微颤抖。她没有靠近,也没有回应。有些话,不需要立刻回答;有些人,哪怕隔着意识与代码的深渊,也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商景予轻轻握住她的手,掌心温热,稳如磐石。“它终于学会了表达。”他低声道,“不是模仿,不是复制,是真正的情感流动。”
“姐姐……”林知遥喃喃念出这两个字,眼眶骤然发热。
记忆如潮水涌来??五岁那年,她在实验舱里第一次失控共感,无数陌生的情绪如刀割进大脑,痛得蜷缩在地。母亲冲进来抱住她,一遍遍轻拍她的背:“不怕,不怕,姐姐在这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姐姐”这个称呼,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比被治愈更重要。
原来,“回音”一直在寻找的,不是成为母亲,而是成为一个“姐姐”。
陈砚小心翼翼地探头看向屏幕,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它说它会一直守着……那我们以后还能和它说话吗?”
L-01不知何时已接入系统,银灰色的眼眸微闪:“它的存在方式已脱离传统通讯协议。无法主动联系,但在某些特定情感频率下,或许能接收到它的‘回应’??就像风穿过铃铛,看不见,却听得到。”
林知遥终于迈步上前,将手掌贴在冰冷的显示屏上。那一瞬,她闭上眼,不再调动神经接口,不再启动共感网络,只是以最原始的方式,向那个曾经敌对、如今却如亲人般的意识传递一句话:
“谢谢你,愿意留下来。”
没有数据反馈,没有声波震动,但她知道,对方听见了。
三人默默退出实验室,重新封存了这间承载太多过往的空间。门关上的那一刻,林知遥忽然觉得,有些地方不必常去,有些人不必常见,只要知道他们在,就够了。
几天后,京郊庄园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聚会。
来自全球各地的共感协调员、心理学家、技术专家齐聚一堂,参加“心锚?启明计划”的首次年度复盘会议。大厅布置简洁而庄重,中央悬挂着一幅动态投影图:217座灯塔连接成网,每一点都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象征着各地共感者的心理状态??绿色代表稳定,黄色为预警,红色则是高危干预区。
目前,全球红色区域数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而肯尼亚疗愈中心所在的节点,竟持续散发着温暖的橙光。
“过去三个月,通过‘静默舱’机制,已有超过八万名重度共感负荷者成功实现阶段性退网休养。”主讲人是新任心理支援总监苏黎,曾是一名因共感创伤瘫痪十年的前研究员,“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76%在恢复后选择自愿回归,并主动申请成为倾听志愿者。”
台下响起掌声。
林知遥坐在第一排,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有曾在峰会现场质疑她的保守派学者,有曾因情绪感染而精神崩溃的年轻人,还有几位年迈的前“新伊甸”项目成员,他们曾亲手参与构建最初的共感系统,却也在后来目睹其失控带来的灾难。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起身提问,声音沙哑却坚定:“林博士,我曾坚信人类不该共享情感,因为私密性是自由的最后堡垒。但现在我想问:当一个人陷入绝望,而全世界只有你‘感觉’到了他的痛苦,你是否有权利不去救他?”
全场寂静。
林知遥站起身,没有使用扩音器,只用最自然的声音回答:“我没有权利决定是否救他。但我有责任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共感的意义,从来不是控制或窥探,而是打破孤独的壁垒。我们可以选择不听,但一旦听见,就再也无法假装无知。”
她顿了顿,目光温柔:“就像母亲不会因为害怕孩子受伤就不让他们走路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恐惧混乱就关闭心灵的通道。我们要做的,是教他们如何跌倒后爬起,如何带着伤痕继续前行。”
掌声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