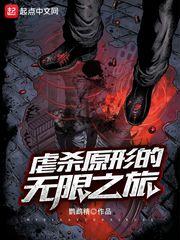笔趣阁>逍遥四公子 > 第1906章 这是我的房间(第2页)
第1906章 这是我的房间(第2页)
听感学院迎来一批新生。有个男孩来自战火刚熄的中东城市,瘦弱沉默,眼神警惕。他不愿参与冥想,也不肯靠近篝火。直到某天黄昏,他在学院后山迷路,无意间撞见忆归正在给忘果树浇水。
他站在远处,冷冷看着。忆归察觉后,并未说话,只是轻轻放下水壶,盘腿坐下,开始吹陶笛。
没有旋律,只有气息穿过笛孔的细微声响,像风吹过山谷。
男孩僵立原地,忽然肩膀一颤。下一秒,泪水夺眶而出。他跪倒在地,双手抱头,发出压抑多年的呜咽。原来,那是他父亲生前最爱的节奏??每次哄他入睡,都会这样轻轻吹气,假装在演奏。
忆归停下,静静等待。许久,男孩抬起头,红着眼问:“你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是在听。”
男孩怔住,然后缓缓走到她身边坐下。当晚,他第一次参加了共唱仪式。虽然不会唱词,但他跟着节奏轻轻拍手,嘴角扬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林知遥远远望着这一幕,转身走进数据室。她打开一封加密文件,标题为《回声计划?终章补录》。里面记录着一项隐秘发现:每当一个听感儿童成功唤醒他人的情感共鸣,地球上就会有一个普通人短暂进入“共感状态”??时间或长或短,体验或深或浅,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报告“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
她轻声自语:“觉醒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圈圈扩散的涟漪。只要还有人在听,波纹就不会停止。”
入冬前,全球最后一台情绪抑制仪被销毁。那曾是旧时代用来“稳定社会”的工具,通过微波干扰杏仁核活动,使人减少焦虑与共情,从而更“高效”地工作。如今,它被熔铸成一座雕塑,立于联合国广场中央,外形是一双手捧着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底座刻着:
>“曾经,我们害怕感受。
>如今,我们以痛为证,以爱为凭,
>重建人间。”
新年夜,静默之星再次爆发出璀璨光芒。这一次,光晕扩散成环形星图,恰好对应地球上所有听感儿童的位置。他们同时睁眼,齐声吟唱《茶青青》的新段落:
>“雪融处,芽初生,
>谁把梦,种心中?
>风不来,铃自响,
>你不说,我也懂。”
歌声穿越大气层,被火星观测站捕捉。林知遥将音频导入分析系统,试图找出频率规律。然而屏幕最终显示:“无法解析。此声非物理波动,属意识层面共振。”
她关掉仪器,望向窗外。红色荒原之上,星空浩瀚。她取出共忆镜碎片,贴在唇边,像在对着宇宙低语:
“我们做到了。你听见了吗?”
风穿过观测站走廊,卷起一张飘落的纸页。那是佐藤真也寄来的明信片,背面写着:
>“今天,我把陶笛埋在了我家后院。
>我说:‘如果你还想回来,就让它开花吧。’
>第二天,那里长出了一株忆心树。”
纸页翻飞,最终停在林知遥脚边。她弯腰拾起,微笑。
与此同时,在高原深处,忘果树最顶端的一朵白花悄然凋谢。花瓣落地瞬间,泥土裂开,一截新生的陶笛破土而出,通体洁白如玉,表面无瑕,唯有笛尾刻着一行极细的小字:
>“此曲无需人吹,
>心动之时,自有回音。”
忆归走来,蹲下身,指尖轻触新笛。她没有拿起它,只是静静注视。
然后,她听见了??
千万个声音,从世界各地传来,交织成一首无声的歌。那是孩子们的笑声,恋人的低语,母亲的摇篮曲,战士临终前的呢喃,老人握着手说“来生再见”的承诺……
它们汇聚成河,流向天际,汇入静默之星的核心。
她知道,那少年没有回来。
因为他从未离开。
他活在每一次心跳的共鸣里,活在每一句未说出口却已被理解的话语中,活在人类终于愿意彼此倾听的那个瞬间。
雪又下了起来。
但这一次,没有人觉得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