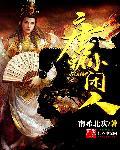笔趣阁>文豪1983 > 第53章 军旅文学的自由王国(第1页)
第53章 军旅文学的自由王国(第1页)
裴顺化的事情死无对证,他自己又受了伤。于是没有受到任何追究,顺利回到河内。
到了河内他才知道,原来“常征”同志还未病故,只是病重得厉害,已丧失了行动能力,因而提前宣布辞去职务。
越南高层陷。。。
雪在凌晨时分停了。我醒来时,窗外灰白的天光映着未化的积雪,像一张尚未书写的信纸。林晚已经不在身边,床头留着一张便条:“去录音棚调最后一版母带,中午回来。”我起身泡了杯热茶,走到书桌前,打开那本《听见》的打印稿。昨夜写完的最后一章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页边有几处我用红笔圈出的修改痕迹??不是语言上的瑕疵,而是情感的迟疑。比如“你不是孤单的”那一句,我曾写下“你从未被遗忘”,又划掉。总觉得太重,像是许诺,而不像回应。
手机震动,是周哲远发来的消息:“沈先生那段录音,我想做成一张限量黑胶,封面用他窗前那株腊梅的照片。你觉得呢?”我回他:“好。但别印‘遗言’之类的词,就写‘他说的话’。”他很快回复一个笑脸。
上午十点,我接到河北小芸的电话。她的声音比往常清亮:“陈老师,村里孩子们录的第二轮故事整理好了,您能听听吗?”我点开她发来的音频链接,第一个响起的是个八岁女孩的声音,她正采访自己的外婆:
“姥姥,您最怕什么?”
老人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最怕听不到小芸叫奶奶了……那时候她妈非让她去城里念书,走那天哭得撕心裂肺,我也跟着掉泪。可我不敢拦,我知道,娃儿得往前走。”
录音里传来小女孩抽鼻子的声音:“那您想她的时候怎么办?”
“我就坐在门口那张竹椅上,晒太阳。听着风刮过葡萄藤,沙沙的,像她在跟我说话。”
我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老屋檐下佝偻的身影,和远处蜿蜒的田埂。这声音没有修饰,没有技巧,却比任何一篇散文更接近真实。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万家录音”最初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宏大叙事,而是这种近乎笨拙的坦诚??人们终于愿意说出“我想你”,而不是“我没事”。
中午林晚回来,手里拎着两个饭盒,还有一只牛皮纸袋。“给你带的。”她说。我打开一看,是一台全新的便携式数字录音机,型号很新,但设计复古,银色机身刻着一行小字:“为不可复制的声音而生。”
“这不是市面发售的机型。”我翻看着,“定制的?”
她点头:“一家音频设备厂听说我们在做‘遗音守护’项目,主动联系,说愿意赞助一批设备给偏远地区的学校。这只是样机,他们想请你试用并提意见。”
我摩挲着机器边缘,忽然问:“你说,十年后,这些录音还会存在吗?云端会崩塌,硬盘会老化,磁带会消磁……我们拼命留下声音,可它们真的能穿越时间吗?”
林晚坐到我对面,轻轻搅动碗里的汤:“也许不能。但重要的是,在那一刻,有人说了,也有人听了。就像沈先生说的,‘留下你的声音’??不是为了永恒,是为了不辜负那个鼓起勇气开口的人。”
下午我带着新录音机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里即将启动首批“家庭倾听实践课”的试点教学。教室布置得很简单,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十几个学生围坐一圈,每人面前放着一部老式录音笔??是学校临时凑出来的,有的还是二十年前的产物,按键泛黄,录音时常断断续续。
课程设计者是一位年轻的心理老师,叫李妍。她向我介绍:“第一节课的主题是‘听父母说一次童年’。我们要求学生回家录制一段至少十分钟的对话,内容不限,但必须是父母主动讲述的往事。”
我坐在角落观察。学生们起初拘谨,有人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打开录音功能。但当第一个女生播放她母亲讲述七岁那年洪水中被解放军救起的经历时,整个教室安静下来。那声音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语速缓慢,偶尔哽咽,背景还能听见厨房炒菜的噼啪声。她说:“那时候我以为我要死了,可那个兵哥哥背着我?水,一直说‘别怕,有我在’。从那以后,我就觉得,世上真有不怕死的人。”
下课铃响了,没人动。有个男生低声说:“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她总说我忙,没空聊天。”
我走过去,把手里的新录音机递给他:“试试这个。不用多,就问一句:‘妈,您小时候最快乐的一天是什么时候?’然后,等她说完。”
他接过机器,手指微微发抖。
第二天,我独自去了香山脚下的一家安宁疗护中心。这里住着十几位生命进入倒计时的老人,其中一位是我大学时代的文学教授,姓赵。他曾教我们读鲁迅、读沈从文,晚年罹患渐冻症,如今已无法言语,只能靠眼球转动与人交流。他的女儿联系我,希望我能完成一次“非语言访谈”??用声音记录他最后的精神世界。
我走进病房时,赵教授正仰卧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见我进来,他的目光缓缓移过来,停留了几秒,像是认出了我。我打开录音机,轻声说:“赵老师,我是陈实。今天不讲课,也不考试,就想陪您坐一会儿。”
我没有提问,只是开始朗读。读的是他当年最爱讲的《边城》片段:“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读完一段,我停下来,房间静得能听见呼吸机的节奏。突然,他的右眼眨了一下??这是他约定的“继续”信号。
于是我继续读,读废名的诗,读里尔克的信,读他自己三十年前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每当他眨眼,我就知道他还“在”。两个小时后,我合上书,轻声问:“赵老师,还有什么想听的吗?”
他久久不动。我以为结束了。可就在护士进来换药时,他忽然用力眨了三下眼??那是“有话要说”的紧急信号。
护士立刻拿来写字板和红外追踪笔。他用尽全身力气,让视线停留在字母上,一个一个拼出一句话:
**“告诉学生……写作不是为了被记住……是为了不让别人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