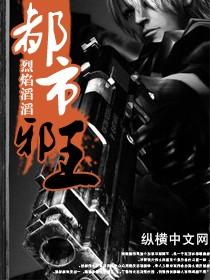笔趣阁>我佛渡我修罗道 > 路有冻死骨(第1页)
路有冻死骨(第1页)
辞别付溪,无定孑然一身,踏上了返回临安的路。
晨雾尚未散尽,末襄城高耸的城门在身后渐渐模糊,如同一个逐渐远去的、充满了挣扎、温情与未解纠葛的梦。他拢紧单薄的僧袍,背上的行囊里除了几卷经文和简单的衣物药石,再无长物。寒风卷起尘土,扑打在他平静却难掩疲惫的脸上。
他的脚步并不快,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缓慢。
并非只因身体初愈,更因每离末襄远一步,心头的沉重便添一分。那并非对某个具体之人的留恋,而是一种更为宏大的、难以排遣的悲悯,在离开相对安稳的城池后,迅速被沿途所见的人间苦难所填充、放大。
刚出城门不过数十里,边陲之地特有的荒凉与肃杀便扑面而来。
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废弃的村落残垣断壁,焦黑的梁木无言诉说着不久前的战火与劫掠。偶尔遇见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的流民,他们眼神空洞,步履蹒跚,如同惊弓之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蜷缩起来,眼中满是惊恐与麻木。孩童的啼哭被大人死死捂住,生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无定停下脚步,将自己仅有的几块干粮默默分给一个抱着婴儿、嘴唇干裂的妇人。
那妇人愣愣地看着他,随即像是反应过来,猛地跪下磕头,却被无定轻轻扶起。他看着那婴儿因饥饿而嘬着手指,发出微弱的哭声,心中如同被巨石碾过。
这就是边疆的子民。守卫着帝国的门户,却最先承受着战乱的撕扯,家园被毁,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所谓的王师,有时带来的并非庇护,而是更大的浩劫。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沉默。悲悯心如同被反复撕扯的伤口,汩汩地流着血。
越往内地行走,战乱的直接痕迹似乎减少了,但民生之凋敝、百姓之困苦,却并未有丝毫好转,甚至以一种更隐晦、更令人窒息的方式呈现。
他途经一些小镇村落,往往十室九空,良田荒芜。
侥幸留下的,多是老弱妇孺,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刨食,眼中看不到丝毫希望。苛捐杂税的名目繁多,压得人喘不过气。
偶尔有看到官吏下乡催逼,态度蛮横,如同虎狼,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或将今年秋收后最后一点活命的种子交出去。
更有一处地界,土匪横行。
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匪徒设卡勒索过往行人商旅。
无定亲眼见到一支小小的商队被洗劫一空,带头的老者跪地苦苦哀求,却被匪徒一脚踹开,扬长而去。而本该保境安民的官兵驻地,却就在不远处的山头上,对此视若无睹?甚至……有百姓私下咬牙切齿地低语:“官匪本就是一家!那些匪徒孝敬够了,官兵自然睁只眼闭只眼!有时,官兵比匪还狠!”
“官不如匪”。这四个字像冰冷的毒刺,深深扎进无定的心里。他站在那片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的土地上,看着百姓眼中对“官”的彻底失望与仇恨,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佛说众生平等,慈悲为怀。可这世间,为何有如此多的不公?为何上位者可以穷奢极欲,视民如草芥?为何本该护佑一方的父母官,却成了盘剥百姓、与匪类勾结的豺狼?
他也曾身处那座权力的巅峰之侧,深知那朱红宫墙之内是何等的勾心斗角、奢靡无度。
皇帝中毒垂危,皇子们争夺不休,朝臣们站队倾轧……
看看这宫墙之外,百姓又是如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
他一路走,一路停。遇到病患,他便上前诊治,分文不取;遇到饥寒,他便拿出化缘得来的微薄食物与衣物分享。
他能做的太少,太少。
杯水车薪,如同试图用一根稻草去阻挡洪流。每一次施以援手,都能换来千恩万谢,可每一次离开,留下的却是更深的无力与痛苦。
夜幕降临时,他常常露宿在破庙或山野之间。燃起一小堆篝火,对着跳跃的火光打坐诵经。经文能暂时安抚躁动的情绪,却无法解答他心中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与挣扎。
自己当初的选择,真的对吗?
放弃那虚妄的帝位之争,皈依佛门,寻求内心的平静与渡世之道。这条路,他走得虔诚而坚定。他以为远离权力中心,青灯古佛,行医济世,便是慈悲,便是修行。
可如今看来,他的慈悲,何其渺小!他的修行,何其无力!
他救得了几个人?能治好他们的身体之疾,可能治好这世道压在他们心头的绝望吗?能改变这官逼民反、匪患横行的现实吗?能阻止边疆的战火与杀戮吗?
若他当年……若他当年没有选择出家,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利用那“前朝太子”的身份,去争,去夺,去攫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否就有可能改变这一切?是否就能肃清吏治,荡平匪患,让百姓真正能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