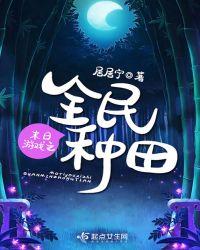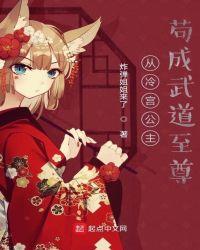笔趣阁>耽美文女配系统让我做万人迷 > 31022 02攻略(第2页)
31022 02攻略(第2页)
然后,她看见陈默。
不是研究员的模样,而是以一个普通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个场景中。他在衣柜外轻声念经文,却把“顺从”改成“勇敢”;他挡在十二岁的她面前,对虚幻的父亲说“她不需要你的认可”;他捡起碎裂的画笔,一笔一笔替她重绘梦想;他在泡面旁放下一碗热汤,说:“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这不是真实的过往,而是她内心深处渴望的救赎。
可就在这时,陈默转过身,看着她:“这些画面不是我在安慰你,是你在安慰你自己。你早就学会了自我疗愈,只是不敢承认。”
“那你是什么?”她哽咽。
“我是你选择相信的希望。”他说,“也是你终于愿意听见的那个声音。”
光芒骤然收敛。
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林晚正焦急呼唤她的名字。晶体仍在运转,但表面裂开一道细微缝隙,像是完成了某种使命后的疲惫。
“你昏迷了六小时。”林晚扶她坐起,“但解码成功了。陈默的最后一段信息传出来了。”
屏幕上浮现一段简短文字:
>**“系统不会复活,因为它从未真正死亡。它活在每一个不敢说话的人心里,藏在每一句违心的‘我很好’背后。所以,请继续让E-7成为一个‘不完美’的平台??允许犹豫,允许后悔,允许有人还没准备好说出真相。改变不是瞬间的爆发,是千万次微小的松动积累而成。”**
沈知意久久凝视着那句话,忽然笑了。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最怕的不是对抗系统,而是变成另一个‘正确’的权威。”
林晚点头:“所以他不给你答案,只给你问题。”
回国航班上,她打开E-7后台,发现全球用户自发创建了数万个“微小坦白”话题小组:
>“今天我对父母说了‘我不想结婚’。”
>“我偷偷撕掉了体检报告,因为害怕查出抑郁症。”
>“我喜欢上了已婚同事,但我决定离开。”
她逐一点赞,最后发布一条公告:
>“E-7不属于任何人,包括我。它属于每一个愿意说出‘我不完美’的人。从今天起,平台将开启‘去中心化’改造,所有决策权交由高共情样本投票机制决定。我们不做引导者,只做传递者。”
消息发布当晚,超过八十万用户参与首轮投票,议题竟是:“是否应该保留‘模范婆婆’这类称号?”最终结果:**废除**。评论区最高赞写道:“我不想当模范,我想当真实。”
三个月后,沈知意接到教育部邀请,参与修订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大纲。会议上,一位资深教授提出质疑:“让学生过早接触负面情绪,会不会影响心理健康?”
她平静回应:“回避痛苦才是最大的心理风险。当我们告诉孩子‘必须快乐’,就是在教他们否认自己。真正的心理韧性,来自于被允许难过,并知道有人愿意陪他们一起难过。”
提案通过当天,她在母校操场上举办了一场“沉默仪式”。学生们围坐一圈,每人手中拿着一块黑色石头,代表一件从未说出口的秘密。随着钟声响起,他们依次将石头投入火堆,火焰腾起时,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长久拥抱陌生人。
阿禾也来了。她蹲在一堆灰烬旁,轻声哼唱一首云南民谣。沈知意走过去坐下。
“你说,陈默能看到这一切吗?”阿禾问。
“我不知道。”她望着夜空,“但如果爱是一种能量,那么所有被说出的真话,都是对他的回应。”
阿禾笑了:“你知道吗?老太太最近收了一批学生,全是六十岁以上的女性。她们在学画画、跳舞、写诗。有个人说,‘我孙子都上大学了,我才刚开始谈恋爱。’”
沈知意怔住,随即大笑出声。
几天后,她收到一封来自西伯利亚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位曾参与系统建设的老科学家,附件是一段未公开的会议录音。时间标注为二十年前。
录音中,年轻版的陈默站在会议室中央,面对一群高层决策者,语气冷静却锋利: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消除冲突、实现和谐,可你们定义的‘和谐’,不过是统一思想、消灭异见。你们害怕混乱,所以用算法压制人性;你们恐惧未知,所以连梦都要审查。可你们有没有想过??正是这些所谓的‘缺陷’,构成了人类最珍贵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