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华娱从男模开始 > 654这波属实恶人先告状(第1页)
654这波属实恶人先告状(第1页)
“小田,今天胃口很好哦!”
吃早餐的时候,李依桐看着吃的明显比前两天要多不少的小田,很是细心地察觉到了对方的开心。
小田咧嘴一笑,倒是挺想跟桐桐姐分享一下自己的开心来着,不过瞥了眼旁边的周。。。
冷芭在戛纳的第三天清晨,酒店外已聚集了十几家国际媒体。她站在阳台上喝着黑咖啡,看着远处海面泛起金光,像极了十年前那个凌晨??她从男模公司逃出来时,东方也正透出这样的微光。那时她肋骨未愈,每走一步都疼得发抖,却仍把一卷偷录的潜规则证据塞进了邮筒。如今那封邮件早已被区块链存证永久封存,而当年那个蜷缩在街角的女孩,正成为全球影坛谈论的名字。
手机震动,林晚舟发来消息:【人社部连夜回应#请让苏婉妈妈得到救治#话题,已成立专项小组督办个案社保补缴问题。医院方面承诺启动绿色通道治疗。】
冷芭轻轻呼出一口气,将咖啡杯放在栏杆上。风很大,吹动她额前碎发,也掀起了日记本的一角。她低头看见昨日写下的句子,指尖轻轻抚过“火种”二字,仿佛怕惊扰了它沉睡的力量。
上午九点,她前往电影宫参加“女性创作者与权力结构”圆桌论坛。会场内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制片人和人权组织代表。主持人开场便播放了一段剪辑视频:中国某影视基地深夜灯火通明,一群群群演蹲在路边啃冷馒头;非洲片场里,女录音师背着六十斤设备徒步十公里;印度一位童星因拒签不平等合约被全行业封杀……画面最后定格在《幕后》片尾那句冰冷的语音:“您所查询的参保记录不存在。”
“我们今天邀请冷芭女士,并非因为她获得了奖项。”主持人说,“而是因为她的电影让无数沉默者第一次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提问环节,一名法国纪录片导演举手:“你的勇气令人敬佩。但我想知道,在那种环境下坚持真实是否意味着自我毁灭?你真的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吗?”
冷芭没有立刻回答。她摘下金蝶胸针,放在话筒前。
“这是我工坊里一个学员做的。”她说,“材料是回收的旧电路板熔铸而成。她说,这些芯片曾经储存过无数谎言、删减过的剧本、被屏蔽的投诉信。但她想用它们造一点美。”
台下安静下来。
“我十六岁那年,被逼签下空白合同的时候,也有人问我同样的话:‘你以为你能活到说出真相的那天吗?’”她声音平稳,“可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暴力,不是威胁,而是慢慢习惯沉默。当你发现周围所有人都低头走路、闭嘴干活,你会开始怀疑??是不是只有我太较真?是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错?”
她停顿片刻,目光扫过全场。
“但我活下来了。不是因为我多坚强,是因为有人在我最绝望时递来一碗热粥,压着纸条说‘我们支持你’;是因为一位老阿姨熬了十年夜粥,只为等一个愿意讲真话的导演回来;是因为一个母亲躺在病床上还在问:‘电影得奖了吗?’”
她的声音微微发颤,却又无比坚定。
“所以我不怕毁灭。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如果我们都不再说话,下一代女孩会不会以为,这一切本来就是正常的?”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日本记者小野写下笔记:【这不是演讲,是一场精神起义。】
中午,冷芭受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文化权益午餐会。席间,多位国际电影节选片人主动提出合作意向,愿为“破茧计划”提供海外展映平台。柏林电影节代表更当场宣布,将《幕后》纳入明年“社会正义影像单元”开幕影片。
“你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电影。”冷芭对众人说,“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份证词。我们收集的每一段录音、每一笔账目、每一个被开除的名字,都在证明一件事:剥削从来不是偶然,它是系统性的设计。”
饭后,她收到苏婉视频留言。镜头晃动,背景是医院走廊。苏婉眼圈仍红,但嘴角扬着笑:“我妈醒了第二次,神志清楚。医生说感染控制住了,接下来只要持续治疗和营养支持就能康复。她刚吃完一碗粥,说味道比工坊的好,但没敢告诉我们是不是真的。”
冷芭回拨过去,接通瞬间,苏婉的母亲虚弱地笑了:“冷导……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站在外国的台阶上,穿着裙子,像明星一样。我就跟护士说,那是我女儿的老师,也是我的恩人。”
“您别这么说。”冷芭眼眶发热,“是您用自己的经历让我们拍出了这部电影。”
老人摇头:“我不是为了电影醒过来的。我是不想死得太悄无声息。那么多姐妹干了一辈子,连名字都没留下。我不想也这样走。”
冷芭握紧手机,说不出话。阳光透过病房窗户洒在床上,照着那双布满针孔的手。
挂断后,她独自走到海边。地中海的浪不大,却执着地一遍遍拍打着沙滩,如同那些年她在剪辑室反复重放的同期声??雨夜里灯光组姑娘们的咳嗽、搬运器材的脚步、对讲机里模糊的指令。她蹲下身,用手捧起一汪海水,任它从指缝流走。
“如果记忆有重量,”她低声自语,“那它一定比黄金沉重。”
傍晚回到酒店,安保团队送来最新报告:那两条恐吓短信的源头已被追踪至境外服务器,伪装成普通用户注册账号,实则关联国内某资本集团海外舆情操控机构。警方已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冷芭暂缓回国行程,考虑人身安全风险。
她看完文件,淡淡一笑:“告诉他们,我该回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当晚,她在社交平台发布动态,配图是周副主任留下的审查纪要复印件局部,特意圈出那句手写批注:“暂不予禁映”。文字只有一行:
【他们怕的不是电影,是观众开始思考。】
这条动态两小时内转发超百万。网友自发制作海报,将“破茧”二字化作蝴蝶形状,翅膀由无数片尾字幕拼成。广州美院学生发起艺术行动,用废弃胶片在城市街头拼贴巨型装置《看不见的人》,主题墙上写着冷芭在戛纳的那句话:“我想成为光。”
第四天,冷芭接受BBC专访。记者问:“你现在被视为某种象征。你觉得这对你是一种成就,还是一种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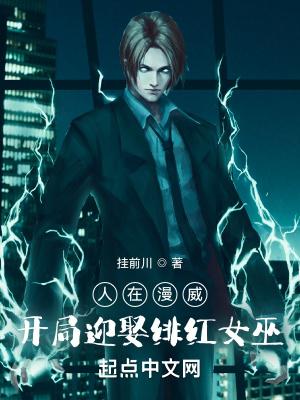

![每个剧本都要亲一下[快穿]](/img/3616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