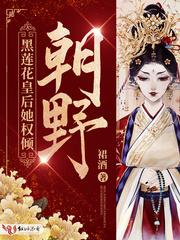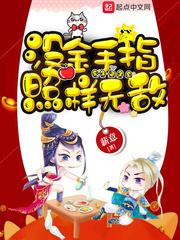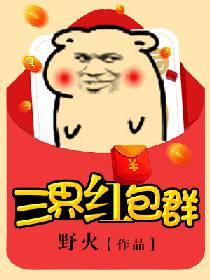笔趣阁>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3章 是的他是陈瑾(第3页)
第493章 是的他是陈瑾(第3页)
然而,风波也随之而来。
某娱乐博主发布视频,标题耸动:“所谓‘非虚构表演’,不过是卖惨营销!林默靠煽情收割眼泪,实则毫无艺术价值!”
评论区迅速分裂。有人力挺:“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真实!”也有人附和:“确实太沉重了,艺术不该这么苦大仇深。”
压力如潮水般涌来。有赞助商临时撤资,有合作机构提出修改课程方向,建议增加“情绪管理”“形象包装”等内容,以迎合市场。
林默没回应任何一方。他只是在当晚的课上,放了一段新素材??是他在康复中心偷拍的一幕:一位失语症患者,用手不断比划着某个动作,家属茫然不解,直到护士忽然明白:“他是想说,‘我想再看一次日出’。”
画面结束,教室一片寂静。
“你们觉得这段能拿奖吗?”林默问。
没人回答。
“它不会获奖。”他说,“因为它没有戏剧性反转,没有催泪BGM,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但它真实存在过。而我们的责任,不是把它变成‘好看’的东西,而是让它‘被看见’。”
他环视众人:“如果有一天,你们的作品被人骂‘太普通’‘没流量’‘不够爽’,你们会怎么办?”
小舟举手:“我会继续拍。因为我知道,有人需要它。”
林默笑了:“很好。记住,观众可以离开,但我们不能背叛信任我们的人。”
一个月后,《光隙》受邀参加南方纪实影像展。展映当天,放映厅座无虚席。结束后,一位白发老人拄着拐杖走上台,握着林默的手说:“我儿子十年前车祸走了,我一直不敢碰他的东西。可看了你们的片子,我翻出了他生前拍的DV,里面全是路边的野花。我现在每天看一段,好像他还在我身边拍照。”
林默眼眶红了:“谢谢您愿意分享。”
老人摇头:“该说谢谢的是我。你们让我知道,思念不是病,是爱的延续。”
展览闭幕当晚,林默独自走在江边。秋风拂面,城市灯火倒映在水面,碎成一片流动的星河。他掏出手机,给陈屿发了条语音:
“你说得对,这条路注定不会轻松。但我现在不怕了。因为我终于明白,我不是在教表演,我是在帮人找回说真话的勇气。”
语音刚发出去,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旋律??是母亲最爱的那首《春之声》插曲。他循声走去,发现江畔广场上,一群老人正在跳交谊舞。领舞的大妈看见他,笑着招手:“哎哟,这不是张桂兰的儿子嘛!你妈以前常来这儿放电影,我们都记得!”
林默愣住。
“来嘛,一起跳!”大妈拉着他,“音乐不停,故事就不该结束!”
他笨拙地跟着节奏转了个圈,引来阵阵笑声。月光洒在脸上,暖得不像秋天。
那一刻,他仿佛看见母亲站在人群外,微笑着鼓掌。
他知道,有些东西从未消失。它们只是沉入岁月深处,等待一次真诚的回望。
回到工作室,他翻开《底片人生》的文档,在第二章开头写道:
>“真正的艺术家,未必站在聚光灯下。有些人一生都在幕后调焦距、换胶片、守夜场,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光。我不是天才,也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终于学会低头看路的人??而在那条路上,我遇见了千千万万个和我一样的灵魂。”
写完,他合上电脑,望向窗外。
晨光再次爬上梧桐树梢,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他,依旧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