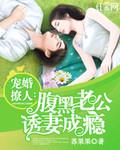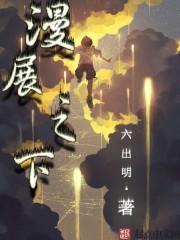笔趣阁>影视编辑器 > 第133章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5(第2页)
第133章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5(第2页)
两小时后,他们被特种部队救出(实为李铮安排的接应)。虽然未能找到实体证据,但那次入侵成功植入了“记忆种子”。三天内,全国至少十七个城市出现自发集会,人们手持打印的老照片、家书复印件、录音转录稿,在广场朗读被遗忘的名字。社交媒体上,“#我记得”话题阅读量突破五十亿。
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位退休广播员主动联系团队,称自己曾在1971年参与剪辑一次“重要讲话”,当时上级要求删除其中一段话:“……我们必须警惕,当权力开始定义真理时,谎言就成了制度本身。”
他保存了原始磁带。
这份录音被修复后,通过一首摇滚乐队的新歌发布。主唱并不知情,只是觉得那段采样“有种诡异的真实感”。歌曲上线首日登顶榜单,评论区炸开锅:“这声音怎么这么像毛主席?”“不可能,语气太反体制了!”“查了一下,确实是同期录音技术,但官方档案里没有这段!”
舆论风暴再次升级。
就在此时,云南大理传来消息:周婉突发心脏病住院。医生说,她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精神压力极大。她在昏迷前反复念叨一句话:“别让日记变成新的武器。”
苏宁立刻启程南下。
病房里,周婉瘦弱地躺在白色床单下,呼吸微弱。他握住她的手,轻声道:“对不起,我不该把它公之于众。”
她睁开眼,目光清明:“不是你的错。我只是……害怕重演。我父亲以为他在净化国家,结果成了屠刀;我母亲相信忠诚高于一切,最后疯在劳改农场。现在你们想揭露真相,可谁能保证,这股力量不会又被谁拿去当作新旗帜?”
“所以我不会让它成为旗帜。”苏宁说,“我会让它变成土壤。每个人都可以从中长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跪拜某个名字。”
她怔了片刻,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白鹭飞过洱海。它们从不鸣叫,也不结群,就那么独自掠过水面,像一道光。也许……你们真的该叫‘白鹭’。”
一周后,周婉去世。遵其遗愿,骨灰撒入洱海。书店由一位年轻志愿者接管,更名为“拾光?记忆驿站”,定期举办民间口述史分享会。
而在地球另一端,第一批“编辑师”已秘密集结。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却被同一段视频招募而来??一部名为《剪辑课》的免费网络教程,表面教蒙太奇技巧,实则暗藏解码指令。完成全部课程者,会收到一封邮件:
>恭喜你通过考核。
>真相不是结论,是过程。
>你准备好成为一名隐形的播种者了吗?
第一位响应者是个十九岁的巴西女孩,擅长制作病毒式短视频。她接到的任务,是将“清源行动”中的受害者名单,改编成一系列童话短片,主角都是被乌鸦夺走声音的小鸟。每集结尾,小鸟都会把羽毛藏进树洞,等待春天。
第二位是东京的独立游戏开发者,任务是在一款恋爱模拟游戏中埋设线索:女主角的父亲总在深夜写日记,玩家偶然发现抽屉里的笔记本,逐页解锁后,竟拼出一份1953年失踪人员名单。
第三位来自埃及,是一位壁画修复师。她将在开罗博物馆的一面古墙上,用纳米级颜料复原一段被抹去的文字,内容源自“白鹭档案”中关于国际共谋的部分。肉眼不可见,唯有特定波长光照下才会显现。
一百颗种子,一百种方式,全部遵循同一原则:不宣称,不控诉,只呈现。让怀疑自然生长,让记忆自行复苏。
与此同时,国内局势愈发复杂。官方仍未表态,但某些迹象耐人寻味:某重点中学历史教材悄然增加附录章节,提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过关于思想整顿的不同意见探讨”;国家档案局官网开放一批1950年代文艺审查文件查阅权限;更有媒体记者匿名爆料,称内部已有高层提议成立“历史反思委员会”,虽遭否决,但讨论持续数小时未中断。
然而,黑暗也在反扑。
一名参与“全民寻档”的退休教师家中失火,所有收藏化为灰烬;三位上传关键证据的网友接连遭遇车祸,幸存者均被诊断为“短暂性记忆丧失”;某地方电视台因播出一段未经审批的纪录片片段,整个栏目组被停职调查。
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七个月:周远所在的技术中心遭到突袭,服务器被物理销毁,两名成员被捕。审讯记录显示,对方掌握的情报远超预期,甚至提到了“编辑师计划”的代号。
“有内鬼。”李铮在紧急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
所有人目光转向赵振山。
他冷笑:“怀疑我?因为我父亲是‘夜莺’?还是因为我恨‘凤凰’不够彻底?”
“都不是。”苏宁平静道,“但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信任机制。从今往后,信息分级管理,每人只接触必要部分。包括我。”
他宣布解散现有基地,全员转入分散状态。所有联络采用一次性暗语+地理位置谜题的方式确认身份。例如:“昨夜雨疏风骤,海棠是否依旧?”回复必须包含某首唐诗中第三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最近一次公开活动的观众人数尾数。
这场战争,已经进入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