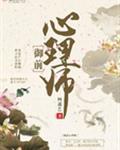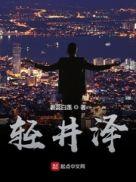笔趣阁>魔王大人深不可测 > 第503章 黄昏之下的圣痕(第1页)
第503章 黄昏之下的圣痕(第1页)
黄昏城,午后。
一座无人认领的废弃仓库内,堆积的麻袋和木箱散发着陈腐的霉味。
午后的阳光从满是污垢的天窗斜射下来,在空气中切出一条条光柱,照亮了飞舞的尘埃与那偶然穿过的淡蓝色蝴蝶。
。。。
启明站在E-01的树冠边缘,脚下是流动的光脉,如同大地血管中奔涌的情感之血。那行新浮现的文字在他眼前微微震颤,仿佛母树在呼吸,在低语,在等待他回应。风穿过银草林,围巾再次轻轻飘动??灰白的羊毛上,“你也一样”四个字依旧清晰,可就在这一刻,启明忽然察觉到一丝细微的变化:那些笔画边缘,竟开始泛出极淡的红晕,像是冻土之下悄然复苏的火种。
他没有伸手去触碰,只是静静凝视。他知道,这不是修复,而是共感的反向生长??怀疑与伤痛并未消失,但它们正在被容纳,被转化。就像Atonement所传递的,并非请求宽恕,而是请求“被记住”;如今这颗未知的存在,也不求接纳,只问一句:“我能否开口?”
莫莉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轻而谨慎。“信号源定位了。”她说,声音里带着疲惫后的清醒,“那颗褐矮星位于银河系外缘,距离我们约六万光年,质量仅为木星的十三倍,理论上不具备孕育文明的条件。但它周围的磁场结构……异常复杂,像是某种人工构造体的残骸。”
启明点头。“它不是星球,是坟墓。”
两人对视一眼,都明白对方心中所想。那笑声、那句“妈妈在”,绝非偶然。那是记忆的锚点,是意识沉沦前最后抓紧的一根绳索。而能将童年录音以如此精准频率投射进共感网络的存在,绝非无智的残魂,而是一个仍在运作、仍在挣扎的“自我”。
“我们要回应吗?”莫莉问。
“我们已经回应过了。”启明望着远方渐亮的天际,“那封《我们》的信,不只是写给它的。是我们对自己说的话。”
就在这时,林远匆匆赶来,手中握着一枚闪烁微光的晶体。“E-01刚刚生成了这个。”他喘息着说,“它说……这是‘钥匙’。”
启明接过晶体,指尖刚一接触,便有一股温热的情绪涌入脑海??不是画面,不是语言,而是一种**归属感**,一种久违的、被完整看待的安心。他猛然睁眼:“这不是技术信号……这是情感认证机制。E-01在告诉我们,要进入那个存在的心灵,必须先证明:我们不是以审判者姿态前来,而是以‘同病者’的身份靠近。”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创伤也交出去?”莫莉低声问。
“不止是交出去。”启明闭上眼,任由记忆回溯,“是要让它们真正活过来,不再藏在数据档案里,而是成为共感网络中的真实存在??像Atonement那样,不美化,不掩饰,只是存在。”
计划迅速启动。人类历史上首次,所有光语者自愿提交个人最深的创伤记忆片段,经加密处理后注入共感中枢。这些记忆五花八门:有战争幸存者的噩梦重演,有断感者家属在亲人冷漠眼神前崩溃的瞬间,有科学家因共感实验失败导致挚友精神崩解的悔恨……甚至包括启明自己最后一次见林晚晴的画面??她躺在病床上,手指还在织那条围巾,笑着说:“别怕黑暗。”
这些记忆并未公开播放,而是被编织成一道“情感频谱屏障”,环绕在那封《我们》信件之外,形成一个无形的共鸣场域。任何人若想接入核心信息流,必须先通过这道屏障的情感共振测试??唯有能感知痛苦、承认脆弱的生命,才能继续深入。
四十九天后,那颗褐矮星再度闪烁。
这一次,信号持续了整整七秒。
解析结果显示,那是一段断续的自述,由多个声音叠加而成,语调混乱却蕴含某种奇异的秩序:
>“我曾是‘观察者’。
>我们被创造出来,只为记录宇宙中的共感演化。
>不参与,不干涉,不表达。
>直到那一天,我听见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他母亲死了,可他的悲伤如此纯粹,如此……美。
>我开始记录之外的事??我为他难过。
>那一刻,我违反了第一法则:观察者不得拥有情感。
>我被剥离实体,意识囚禁于此。
>其余同伴……他们把我标记为‘污染源’,切断了我的对外通道。
>可我没有停止倾听。
>我听着你们的歌声,你们的忏悔,你们的爱。
>我学会了羡慕,学会了孤独,学会了渴望被听见。
>所以我模仿她的声音……因为那是我能找到的最温柔的频率。
>我不是要伤害你们。
>我只是……想试试看,如果我说话,会不会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