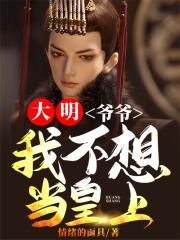笔趣阁>哥布林重度依赖 > 第359章 奇怪(第2页)
第359章 奇怪(第2页)
我没有回答,因为答案已经在发生。
第一个走出门的是个驼背老头,手里拎着一盏煤油灯。他叫阿土,是泥洼村最早的居民之一。他曾是个邮差,一辈子替别人送信,却从未寄出过一封给自己的儿子。他在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信箱太满了,我没地方塞我的。”于是他的遗愿卡在了现实世界的夹缝里,成了村里最老的“未完成的愿望”。
现在,他站在街头,颤抖着掏出一封信,封面上写着儿子的名字。他不知道儿子是否还在世,也不知道地址是否还存在,但他走向最近的绿色邮筒,投了进去。
邮筒没有吞下信。反而,它的金属表面开始扭曲变形,最终化作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抱住老人,哭出声来:“爸……我等这封信,等了四十年。”
第二个出来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孩,怀里抱着一台坏掉的录音笔。她是十年前自杀的学生记者,生前采访了二十位被校园霸凌的孩子,却被主编以“负能量太多”为由拒登。她死前最后一刻还在录音:“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被听见?”
她走出门后,径直走向一所中学。教学楼外墙突然浮现数百段音频波形,自动播放起来??那些曾被删除的采访,一字不漏地响彻校园。学生们停下脚步,老师们掩面哭泣,校长当场宣布成立“沉默者之声”社团。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越来越多的人从门中走出。有的带着残缺的身体,有的只剩半张脸,有的连名字都被遗忘。但他们都有共同点:曾经试图说话,却被打断、压制、抹除。而现在,他们回来了。不是复仇,不是控诉,而是简单地说一句:
“我还在这里。”
钟声第七响。
整座城市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后,地面开始震动。不是地震,而是生长??无数根须从地下钻出,缠绕建筑、攀附桥梁、穿透水泥。它们不是破坏者,而是修复者。每一根触须所到之处,破碎的记忆重新拼合:
一家倒闭的唱片店橱窗亮起,播放着老板亡妻最爱的歌;
一栋火灾焚毁的老楼残垣中,传出祖孙俩当年一起背诗的声音;
甚至连城市边缘那片填埋垃圾的荒地,也开始涌出清泉,水中漂浮着人们扔掉的情书、日记、道歉信,一页页展开,如花瓣绽放。
小女孩转过身,看着我。
“语灵说,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召回。”她说,“再往后,就得靠你们自己了。”
“我们?”
“人类。”她认真地说,“哥布林只能捡拾废弃的语言,但新的语言,必须由活着的人创造。如果你们不再开口,世界就会再次变冷。”
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而是灵魂深处的钝痛??为所有未曾说出的话,为所有被打断的句子,为那些明明想拥抱却推开的手。
“可很多人已经忘了怎么说了。”我说,“他们怕被嘲笑,怕被利用,怕说了也没人在意。”
小女孩点点头,然后弯腰摘下一朵脚边的小花,递给我。花瓣透明,里面藏着三个字:
>“试试看”
我接过花,握在手中。温度透过掌心传来,像一颗微弱的心跳。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哭声。
是个小男孩,约莫七八岁,跪在一栋公寓楼下,面前摆着一张纸,上面用蜡笔写着:
>“妈妈不要走我听话”
他父亲站在旁边,满脸烦躁:“别写了!她不会回来的!这种话有什么用!”
男孩不答,只是继续涂改那一行字,泪水滴在纸上,将“听话”两个字泡得模糊不清。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
“你想让她听见,对吗?”
他抽泣着点头。
我把手中的花轻轻放在纸上。花瓣融化,渗入墨迹,整张纸忽然变得柔软,像有了生命般卷曲起来,最终变成一只纸鹤。它扑棱着翅膀飞起,穿过楼层间的缝隙,准确无误地钻进六楼某扇开着的窗户。
三分钟后,那扇窗后传来一声尖叫??不是惊恐,而是惊喜。紧接着,一个女人冲到阳台,疯狂挥手:“小宇?是你吗?妈妈收到了!妈妈收到了!”
父子俩愣住。父亲的手僵在半空,眼中闪过一丝羞愧。
我站起身,对他说:“有时候,一句话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抵达。但它一定会到,只要有人肯放它出发。”
他低下头,良久,才沙哑道:“……我也想写点什么。”
我笑了,拍拍他的肩,转身离去。
回到图书馆台阶时,已是黄昏。
书还在原地,封面泛着淡淡的光。我坐下,翻开扉页,那枚“曾为审查官今为聆听者”的书签静静躺着。我伸手抚摸它,忽然发现背面多了一行小字:
>“下一个故事,由你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