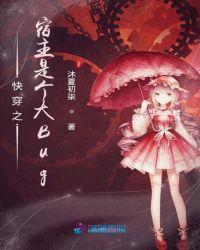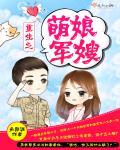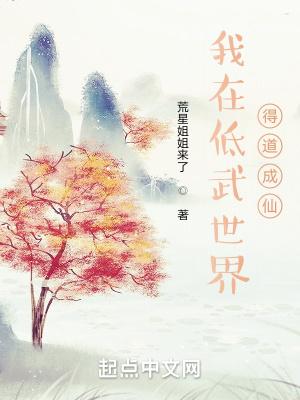笔趣阁>三国:朕,袁术,大汉忠良 > 第三百三十七章 不复此仇枉作人今覆伪齐告英灵(第1页)
第三百三十七章 不复此仇枉作人今覆伪齐告英灵(第1页)
。。。。。。
车将军,这也有他的道理?
迎着众人征询要不要即刻动手的视线,单福却像因车胄之死,受到了刺激般。
“刘玄德,安敢害我家将军!”
他勃然大怒,似冲动之下,当即率着。。。
章会的葬礼之后,定陶城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寂静。不是哀恸到失声的那种死寂,而是一种深沉的、仿佛大地屏息的静谧。百姓们没有敲锣打鼓地送行,也没有焚香烧纸的喧嚣,而是自发地捧着书本走上街头,在政学堂门前排成长长的队列。有人抱着《千字文》,有人拿着《算术启蒙》,还有孩子用稚嫩的手指翻着油印的《公民常识》。他们不言不语,只是静静地将书页轻轻合上,放在那块刻着“薪尽火传”的青石前,然后默默转身离去。
那一日,南北两京同时降下半旗。洛阳太学停课三日,学生们在“新生林”中点燃蜡烛,围坐诵读章会遗章。幽州技学会的工匠们停工一日,将最新研制的风力提水机图纸铺展于地,集体默哀。就连远在西域经商的南方商队,也在敦煌驿站停下驼铃,取出随身携带的课本,齐声朗读《论语》中的“有教无类”。
三年后,联邦议会迎来第一届普选。
这场选举震动天下。五十六州共推选出百名议员,其中竟有三十七人为女性,十二人出身胡族,更有五位曾是奴婢或战俘。当第一位女议员??那位被称为“铁笔娘子”的代县令柳氏??身着素袍登上议政台时,全场肃立。她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钉:
“我七岁为婢,每日扫地挑水,不得识字。十三岁那年,主人家公子念《孟子》,我躲在窗下偷听,被发现后鞭笞三十。血流满地之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若我能读书,必不让他人再受此苦。今日,我站在这里,并非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想读书的孩子,都能堂堂正正走进学堂。”
话音落下,议会大厅内久久无人言语。良久,一位来自辽东的老将军起身,解下佩剑,双手奉上:“此剑随我征战二十年,杀人无数。今献于议会,愿化剑为犁,铸成十万支铅笔,送往北疆义塾。”
自此,联邦进入新政纪元。
教育改革持续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全面落地,各地设立“流动讲学团”,由退休教师、医者、农技师组成,骑驴驾牛穿行于山野村落。每至一地,便在祠堂或庙宇设临时课堂,白日教童蒙,夜间授成人。许多老农起初不信:“认得几个字就能多打粮食?”可当他们亲眼看见邻村用《农事历》精准安排播种,亩产翻倍;又见识了黄月英团队推广的“双层煤炉房”,寒冬时节室内如春,孩童不再冻病夭折,便纷纷牵儿带女前来报名。
更令人惊叹的是科举制度的蜕变。
昔日科举只考诗赋经义,如今则分为“文治”“理工”“医卫”“农政”四大科。考生无论出身贵贱,皆可报考。考场设于各地太学院分院,试题公开透明,答卷匿名密封。第一场为通识测试,涵盖基础算术、地理常识、民法条文;第二场依专业分卷,如“理工科”需设计一座灌溉水渠,“医卫科”要现场诊断三种常见病症;第三场则是实践考核,考生须在指定村庄服务一月,由村民评分。
某年春闱,一名盲人少年引动朝野轰动。他名唤陈明远,幼时因疫失明,靠母亲口述《千字文》启蒙,后得赵元晦资助入盲文学堂,以竹针刻字苦读十年。殿试当日,他以特制盲文答卷完成全部试题,尤其在“农政实务”中提出“坡地梯田+雨水收集+蚯蚓堆肥”三位一体改良方案,被考官评为“近三十年最优策论”。最终,他被任命为黔中道劝农使,三年内率众开垦荒地八万亩,建蓄水塘三十六座,百姓呼其为“天眼大人”。
与此同时,科技之光如星火燎原。
黄月英虽已年过七旬,仍亲自主持“北方技学会”。她带领胡汉青年研制出“雪地滑轮车”,可在积雪深厚的草原快速通行;改进“蜂窝煤炉”,使取暖效率提升三倍;更发明“冰面钻井取水器”,让冬季牧民不再为饮水奔波。最令人称奇的是她指导学生完成的“风力电灯原型机”??利用大型风车带动铜线绕轴旋转,产生微弱电流,点亮炭丝灯泡。虽仅能持续半炷香时间,却已在雁门关外的小村试验成功。当第一缕不属于火把或油灯的光芒照亮土屋时,全村老少跪地叩首,以为神迹。
黄月英闻讯笑骂:“非神迹,乃人力!记住,科学不怕失败,只怕停止尝试。”
文化交融亦日益深入。
在并州混居屯田区,汉胡通婚已成常态。孩子们从小双语并行,既能背诵“床前明月光”,也会唱鲜卑古谣“苍狼引路归故乡”。每逢节庆,双方共办“文武大会”:上午比试射箭、摔跤、马术,下午则进行书法、算术、辩论赛。有一年元宵,一位混血少年以《论“孝”在胡汉家庭中的异同》为题夺冠,他在文中写道:“我父说跪拜是孝,我母说陪伴是孝。后来我明白,真正的孝,是让父母都能听懂彼此的语言。”
连司马懿最后一个门生??名叫裴秀的年轻人??也彻底转变。他曾坚信“乱世唯权谋可存”,如今却埋首绘制《天下舆图》。他走遍山川河流,测量经纬高程,首创“计里画方”制图法,将全国地形精确标注。当他把长达十丈的地图铺展于洛阳太学讲堂时,激动落泪:“先师教我察人心,今我以图观天下。原来治国不在权术纵横,而在知晓每一寸土地上的百姓如何活着。”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风平浪静。
西凉一带仍有豪强抵制新政。他们封锁道路,禁止义塾开课,甚至私设刑堂惩处“叛逆”。更有甚者,勾结残余军阀,暗中训练死士,意图刺杀推行改革的地方官。一名女教员在赴任途中遭伏击身亡,临终前紧抱课本,血染《百家姓》扉页。
消息传来,举国震怒。
联邦议会紧急召开特别会议。有人主张派“国民护土军”镇压,有人建议暂停西部改革以免激变。唯有来自羌族的新任议员阿?起身反对:“刀兵只能压服肉体,却无法唤醒灵魂。我们若以暴制暴,岂非背离袁公路初衷?”
她提议派遣“文卫队”深入西凉,不带武器,只携书籍与种子。每到一村,先帮百姓治病、修渠、教儿童识字,再召集长老座谈,讲解《民法简述》中“人人平等”之义。若有抗拒,则耐心等待,直至民心自悟。
议会最终采纳此议。
第一批“文卫队”由五十人组成,包括十名女医师、十五位教师、二十位农技师。他们徒步穿越戈壁,风沙磨破衣衫,干渴裂开嘴唇,却始终高举写着“知识即光明”的旗帜。起初村民闭门不出,狗吠如雷。但他们日日前来,为老人诊病,替孩童剪发,帮妇人挑水。一个月后,终于有位老妪悄悄收留他们过夜。又过半月,村中少年开始偷偷跟读《三字经》。
半年之内,西凉二十三村相继开门迎教。那些曾设刑堂的豪强见大势已去,或逃亡塞外,或主动交出土地,请求宽恕。其中一人跪在义塾门前痛哭:“我祖上三代为官,自诩书香门第,却不曾想到,真正读书之人,竟是这般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