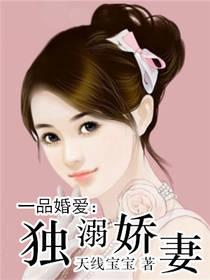笔趣阁>活人深处 > 第747章 原始地牢(第2页)
第747章 原始地牢(第2页)
节目结束后的凌晨两点,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
画面显示一间狭长走廊,墙壁泛黄,挂着褪色的儿童画。时间戳显示:1983年4月12日,上午九点十五分。
镜头晃动,似乎是由手持设备拍摄。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匆匆走过,怀里抱着一名瘦弱男孩。男孩脸上贴着电极片,眼神空洞,但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什么。
女人将他推进一扇标有“静修室A”的门内,随即锁上。
就在门关上的瞬间,男孩突然回头,直视镜头。
那一眼,穿透了三十七年的光阴,刺进我的瞳孔。
紧接着,画面右下角浮现出一行手写字体,像是被人用铅笔匆忙添上去的:
>**苏婉清,城南纺织厂宿舍三号楼402室。她不是母亲。她是护士。但她偷改了我的药单,让我多活了两个月。她说:‘你要记住外面的槐花香。’**
我浑身发冷。
己五十八的母亲?不,她是护士?那枚纽扣……难道不是母爱的遗物,而是一个医者对实验品最后的温柔?
我立刻抓起外套冲出门外。天还未亮,街道空荡,路灯昏黄如旧梦。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纺织厂宿舍,皱了皱眉:“那儿早拆了,现在是商业广场。”
“那附近还有人住吗?”
“养老院倒是有一家,叫‘晚晴园’,收留些孤寡老人和失智症患者……你找谁?”
我握紧口袋里的纽扣:“一个叫苏婉清的女人。”
三个小时后,我站在“晚晴园”三楼的一间病房门口。
护工认出了我:“您就是前几天来过的那位记者?老太太昨晚开始一直念叨‘儿子回来了’,还把那枚旧纽扣擦了十几遍……您真说对了,她确实有个孩子,但早就……没了。”
“怎么没的?”
“出生就查出神经系统异常,送去疗养院做康复治疗,结果再也没回来。她一直不信,每年清明都往那个方向寄一封信。”
我推开门。
苏婉清坐在轮椅上,背对着窗户。晨光洒在她银白的发丝上,像落了一层霜。她手里攥着那枚纽扣,一遍遍擦拭,动作轻柔得如同抚摸婴儿的脸颊。
我没有惊动她,只是静静站着。
过了许久,她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
“你是来找他的吧?”
我心头一震:“您……知道我会来?”
她缓缓转过头,目光落在我的脸上,竟没有一丝浑浊。
“我知道你们都会来。”她说,“每隔几年,就有年轻人来找他。有的拿着照片,有的拿着病历,还有的……什么都不拿,只说‘我梦见了一个穿红线的孩子’。”
她抬起手,指向床头柜上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年轻女护士,怀里抱着一个瘦小的男孩,两人笑得灿烂。男孩手腕上,缠着一根细细的红绳。
“那是我。”她说,“那是他。他们说他是残次品,不能算人。可我知道,他会笑,会疼,会害怕打针时闭上眼睛……他会爱。”
泪水无声滑落。
“我改了他的药单,让他少受点苦。我也偷偷教他认字,给他讲故事。他说最喜欢听《小王子》,尤其是那句‘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他们发现了。”她闭上眼,“他们把我调走,把他……送进了B区最深的地方。再后来,整个项目封存,所有人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记得您。”我说,“他临走前托我带话??他说谢谢您让他记得槐花香。”
老人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他还说了什么?有没有说……他恨不恨我?明明可以救他,却只能躲在角落里改一张药单?”
我摇头:“他没有恨。他说,你是唯一一个肯看他眼睛的人。”
那一刻,她崩溃地哭了出来,像个终于等到道歉的孩子。
我陪她坐到中午。临走前,她把那张照片塞进我手里:“替我烧给他吧。告诉他……妈妈对不起他,但妈妈从来没有不爱他。”
我点头,将照片小心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