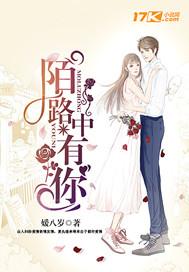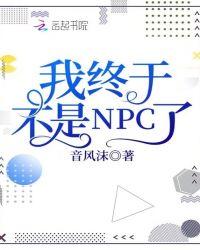笔趣阁>虎贲郎 > 第712章 愿赌服输(第2页)
第712章 愿赌服输(第2页)
“你可知朕为何迟迟不下诏平反?”他开口,声音沙哑。
“因为怕。”少年答。
“怕什么?”
“怕一旦承认错误,王朝根基动摇。”
皇帝默然良久,忽而苦笑:“你说得对。可现在,我不怕了。不是我不怕,而是我发现,真正动摇江山的,从来不是揭露真相的人,而是掩盖真相太久的沉默。”
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宫外万家灯火。
“朕已命礼部拟议,追赠虎卫第七旅‘忠烈虎卫’称号,赐谥‘义贞’,子孙免徭役三代。龙首涧祠庙扩建为国家级祀典,每年冬月十九,由地方官主祭。”
少年静静听着。
“你还想要什么?”皇帝问。
“开放皇室密档馆全部卷宗。”少年说,“允许民间学者自由调阅,设立独立修史局,不受政令干预。”
皇帝皱眉:“这等于割裂君权对历史的掌控。”
“可历史本就不该属于君王。”少年直视他,“它属于每一个曾为之流血、为之守望的人。您今日能改,是因为民心已不可违。若您再拖,下一个站出来的人,或许就不会像我这样只想讲道理了。”
殿内烛火摇曳,映照君臣二人影子投于墙上,竟如对峙又似并肩。
良久,皇帝提笔批红:“准奏。”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三个月内,全国各地涌现三百余所新型守约塾,不再局限于山村野舍,而是进入城镇街巷,甚至有富商捐资兴建“信义书院”。孩子们不再只是背诵《守约铭》,开始学习如何查证史料、辨析真伪、撰写民间纪事。
而在南方,百童送史团已沿江行走八千里。最小的孩子仅九岁,背着一段《龙首涧日记》走村串户。他们在晒谷场搭台演讲,在渡口为船夫吟诵,在茶馆角落表演皮影。每到一处,便留下一枚刻字陶片,上书“虎卫曾在此被记住”。
赵校尉之名渐渐淡去。北疆巡察使职位空缺半年未补,传言他死后冤魂不散,夜夜听见山谷回荡《守约谣》。边境村落悄悄重建守约塾,墙上挂的不再是画像,而是由幸存老兵口述还原的战场地图。
这一年冬天,少年重返敦煌。
风雪再起,昆仑隐没于云雾之间。书院废墟上,新筑的石基已然成型。苏婉儿站在工地中央,指挥弟子们搬运碑石。见到他归来,她只是笑了笑,递过一杯热茶。
“我们准备重建。”她说,“不只是书院,还有‘七钥传承’的仪式。”
“哪七钥?”他问。
她逐一列出:
“第一钥,是记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
第二钥,是文字??所有档案与书信;
第三钥,是器物??遗物、兵器、生活用具;
第四钥,是艺术??壁画、歌谣、皮影戏;
第五钥,是教育??守约塾与流动讲团;
第六钥,是制度??独立修史局与档案公开法;
第七钥,是人心??千万普通人愿意相信并传递真相。”
少年听罢,久久无言。
“原来你早就明白了。”他轻声道,“七钥不在昆仑,而在人间。”
当晚,他们在新书院的地基上点燃篝火。百余名弟子围坐一圈,轮流讲述自己加入守约之路的故事。有人的父亲死于清言司暗杀,有人的母亲曾亲手埋葬跳崖战士的遗体,有人只是在一个雨夜听了场皮影戏,从此再也无法假装不知。
轮到少年时,他取出那枚寒玉碎片,置于火光之上。
“我曾以为,我的使命是找到钥匙,打开大门。”他说,“后来我才懂,门一直开着,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了背过身去。我们的工作,不是破门,而是点亮灯火,让人愿意走进来。”
火焰跳跃,映出每个人眼中的光。
就在此时,一名快马疾驰而至,带来江南急报:林素心病重,自知不起,唯愿再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