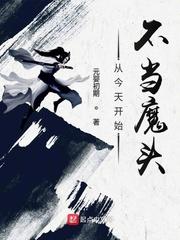笔趣阁>我在西游做神仙 > 第二十二章 义薄云天(第2页)
第二十二章 义薄云天(第2页)
全场寂静。
片刻后,林小满率先跪下,双手合十,低声说道:“我相信。”
紧接着,第二人、第三人……七十二位善首相继跪地,齐声诵念:“我相信。”
声音如潮水扩散,通过飞鸟传书、驿站快马、游方僧侣,迅速传向四面八方。东海岸边,渔民放下渔网,面向西方合掌:“我相信。”西域沙漠,驼队停下脚步,领队仰望星空:“我相信。”北疆雪原,守城将士脱盔叩首:“我相信。”南岭深山,峒寨长老击鼓三声,全族老幼齐呼:“我相信。”
一夜之间,九洲同声。
当最后一道声音落入大地,愿槐幼苗猛然爆裂??不是毁灭,而是蜕变!无数金色光点自裂开的树干中升腾而起,化作漫天星辰般的萤火,洒向人间每一个角落。那些曾挂过金叶的家庭,窗前忽然亮起微光;那些行善之人,梦中听见孩童笑声;连最偏远的村落,井水都变得甘甜清澈。
而那道黑缝,则在亿万声“我相信”中剧烈收缩,最终化为一点黑芒,被新生的愿槐幼苗吸入根系。一声清越鸟鸣自地下传出,似凤非凤,似鸾非鸾,却是传说中唯有“愿火重燃”才会现身的**心鸣雀**。
黎明破晓时,原地已不见幼苗,唯有一棵通体晶莹的玉树静静矗立,枝干透明如琉璃,内里流淌着金色液态光芒。树冠之上,悬着一颗缓缓旋转的光球,形如心脏,搏动之间,散发温暖律动。
青年站在树前,身影逐渐变淡。
“我完成了使命。”他说,“从此以后,不再需要代言人,不再需要讲道台。愿力已融入人间呼吸,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就像阳光照耀大地,并不需要宣告自己存在。”
林小满含泪问道:“你会消失吗?”
“不会。”青年微笑,“只要还有人愿意伸手扶起跌倒的孩子,只要还有人为陌生人撑一把伞,我就会以千种形态归来??可能是街头一碗热汤,可能是寒夜里一句问候,可能是一个无声的拥抱。”
他的身体化作光尘,随风散去,最后一句话落在每个人耳畔:
“记住,你们才是神仙。”
十年过去。
玉愿槐已成为圣地,却不复昔日喧嚣。人们依旧前来,但不再祈求奇迹,而是带着自家孩童,讲述那些关于庄衍、关于初心院、关于一场场平凡却伟大的善举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眼中闪烁着光芒。
而在西岭深处,林小满建了一座简陋书院,名为“信园”。这里不教经义,不授神通,只让学生每日记录一件身边的好事,无论大小。每月十五,师生齐聚院中,将这些纸条投入炉中焚烧,灰烬随风而去,据说能滋养玉愿槐的根系。
某日,一名少年递来纸条,上面写着:“今日帮邻家阿婆挑水五担,她哭了,我也哭了。”
林小满读罢,笑着点头:“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她会哭吗?”
少年摇头。
“因为她太久没被人当作‘重要的人’了。”林小满轻声道,“我们的善,不只是救人,更是告诉对方:你值得被温柔对待。”
少年若有所思。
当晚,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花海中,远处走来一位白发老者,手持拐杖,肩披星光。老者对他微笑,说:“谢谢你记得她。”
醒来后,少年发现枕边多了一枚晶莹的花瓣,花瓣上浮现出两个字:
**回应**
又三十年。
林小满寿近百岁,卧床不起。临终前,他让人将自己抬至窗边,遥望东方。那里,玉愿槐的光芒正穿透晨雾,照亮千家万户。
弟子跪在床前,哽咽道:“老师,若您有遗言,请留下。”
林小满缓缓摇头,嘴角带笑:“我没有遗言。因为我从未离去。看看窗外吧??每个清晨点亮灶火的人,都是我在呼吸;每个雨天为路人让伞的人,都是我在行走;每个对孩子说‘别怕,我在’的大人,都是我在说话。”
他闭目前最后一句是:“告诉后来者,不要寻找神仙。你们本来就是。”
话音落下,屋内忽有清香流转,窗外玉愿槐一片叶子无风自动,轻轻飘落,恰好覆盖在他额上。叶面浮现三字:
**已在**
自此,世间再无“初心院”三字碑,也无“明心台”旧址,更无任何供奉庄衍或林小满的庙宇。但在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家的厅堂里,多了一幅简单的画:一盏灯,一棵树,一个人扶起另一个人。
画下常题一行小字:
>“光,从来不怕少。”
每逢新春,孩童们最爱玩一种游戏,叫做“点灯”。他们用纸折成灯笼,写下新年愿望,挂在村口老槐树上。长辈不说破,只笑着看。
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信仰,不必命名,也能永恒;
有些人,从未飞升,却早已超越神仙;
而这片土地之所以长存希望,并非因为有过英雄,
而是因为总有凡人,在黑暗中,固执地捧着一豆灯火,走向下一个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