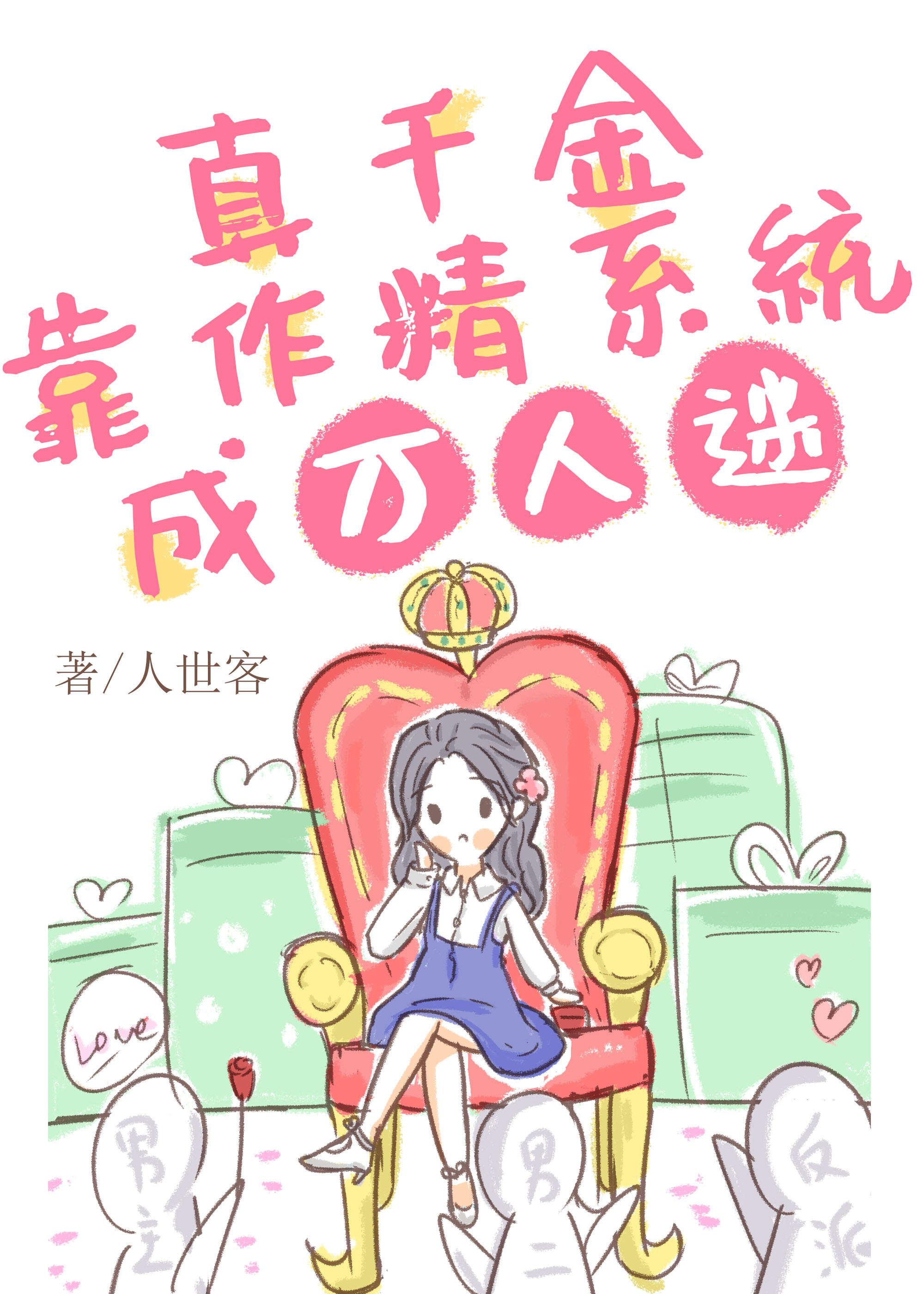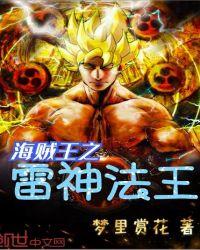笔趣阁>塌房?我拆了你这破娱乐圈 > 第496章 微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第1页)
第496章 微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第1页)
七家公司起诉,对于微讯来说不痛不痒,但问题在于这个风向十分危险。
一家他们不怕,七家也不过是七只蚂蚁,要是十家二十家三十家甚至一百家呢?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一旦形成一股趋势,微讯也要。。。
海平面在黎明前微微震颤,仿佛有巨兽正从深渊缓缓抬头。周念坐在礁石上,吉他横放在膝,手指无意识地拨动琴弦,音符随潮声起伏,不成章法,却与远处海底星钟的脉动隐隐同步。他不知道自己弹了多久,只知道沙粒已浸透露水,脚底凉意顺着血脉爬升至心脏。
突然,一根弦断了。
清脆的崩响划破寂静,像某种信号。他怔了一下,低头看着那根垂落的金属丝,忽然笑了。这不是第一次断弦??十年前在废墟剧院唱《塌房》时,最后一场演出中途也断过一根。那天暴雨如注,观众寥寥,可就在弦断的瞬间,后台瓦砾堆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哭声,紧接着是合唱。现在想来,那不是巧合,是回应。
他没换弦,而是将吉他轻轻放回身侧,闭眼倾听。
风中有声音。
不是语言,也不是旋律,而是一种低频的、近乎呼吸的震动,从海底升起,穿过岩层,渗入骨髓。那是星钟在“说话”。它不再需要翻译,也不再依赖设备解码。只要心还跳着,就能听见。
“你来了。”
这句不是他说的,也不是谁说的。它像是空气本身吐出的一口气,自然而然地浮现。
周念睁开眼,看见海水退去三丈,露出一片平坦的海床。上面布满了发光的纹路,如同血管般蔓延,汇聚成一座巨大的圆形图案??和昆仑塔中枢投影中的星图完全一致。而在图案中心,立着一块石碑,表面刻着一行字:
>“归来者无需名字。”
他站起身,赤脚走向海边。每一步落下,脚印都泛起微光,随即被涌上的潮水带走。当他踏入浅滩时,整片海域忽然安静下来。浪停了,风止了,连海鸟的鸣叫都消失了。只有那股震动仍在,越来越清晰,像是某种召唤。
他继续前行,水漫过小腿、膝盖、腰际。寒意刺骨,但他不冷。相反,体内有种温热在苏醒,像是沉睡多年的火种被重新点燃。
直到海水淹没胸口,他仍未停下。
肺部开始灼痛,意识逐渐模糊,可就在即将窒息的刹那,一道光自海底射出,将他整个人托起。那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上升,更像是空间本身在他周围折叠、重组。他的身体变得轻盈,感官却异常敏锐??能听见鱼群游动时鳞片摩擦的声音,能感受到千米之下火山口岩浆流动的方向,甚至能“看”到大气层外启明号跃迁留下的尾迹。
然后,他站在了一片草原上。
阳光温暖,风吹草低,远处有溪流潺潺。这里没有天穹的概念,头顶是一片流动的星河,星辰如雨滴般缓缓坠落,又在触及地面之前化作花瓣飘散。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有的画画,有的写诗,有的只是静静望着远方。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汉服、中山装、西装、未来感十足的银色制服……但脸上都有着相似的神情??平静,且带着一丝怀念。
“欢迎回家。”一个老人走来,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封皮上写着“陈默父亲”四个字。
周念认得那笔迹。他曾无数次在父亲遗物中见过。
“你是……?”
“我是守灯人之一。”老人微笑,“也是你童年时,在梦里教你哼那首歌的人。”
周念心头一震。五岁那年,他发高烧昏迷三天,醒来后就会唱一首谁都没听过的曲子。母亲以为是胡言乱语,可后来发现,那段旋律竟与一段远古岩画上的符号频率完全吻合。医生说是幻觉,但他知道不是。
“我们一直在等一个‘开口’的人。”老人说,“不是最有天赋的,也不是最成功的,而是那个愿意为一句歌词流泪、为一段旋律停下脚步的人。艺术从来不是装饰,它是人类灵魂的锚点。当记忆消散时,唯有情感还能穿透时间。”
周念低头看自己的手,发现掌纹间浮现出细小的光丝,正缓缓延伸,连接向四周的人。每一根线的尽头,都是某个曾因创作而受伤的灵魂:那个被网暴致死的独立导演,那位坚持用濒危语言演唱民谣的老歌手,那个拍下战争孤儿眼神却被平台封号的摄影师……
他们都活着。在这里,在光里,在彼此的记忆中。
“你们……都是死去的人?”
“不。”老人摇头,“我们只是选择了另一种存在方式。每当有人真心为一首歌哭泣,我们就多一分重量;每当有人写下一句打动自己的诗句,我们就多一寸土地。这片草原,是由千万次‘不忍’堆砌而成的。”
远处,一个小女孩正在教一群孩子唱歌。她穿着蓝裙子,正是林小满在深海画面中描述的那个“梦境导师”。歌声响起的瞬间,周念感到胸口一阵悸动??那是《雪夜》最初的版本,未经修饰,没有编曲,只有一个少年干涩却真挚的嗓音。
“这不是录音。”老人轻声道,“这是共鸣的回放。你在现实世界唱过的每一句,都会在这里重演,成为新来者的启蒙。”
周念忽然明白了什么:“所以……我不是被选中,我是被‘召回’?”
“你从未离开。”老人望向星河,“你的第一首歌,就是在这里学会的。那时你还不会说话,只会用哭声表达悲伤。可当你第一次对着月亮哼出调子时,这片草原长出了第一朵花。”
泪水无声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