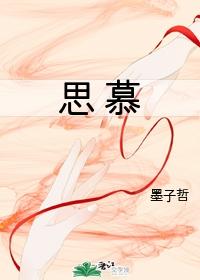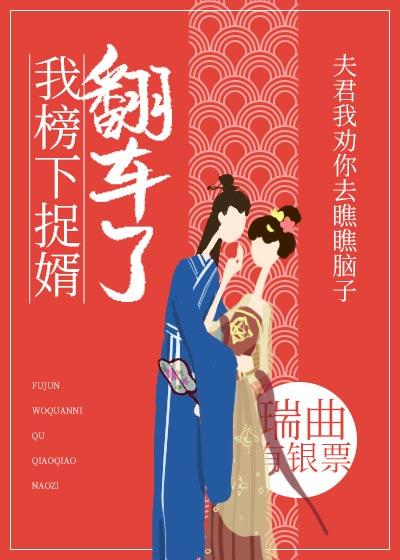笔趣阁>大雪满龙刀 > 0483谋局(第2页)
0483谋局(第2页)
>“可若无人敢言,谁来做那人?”
少年驻足良久,忽觉脚边泥土松动。一株忆辉笋破土而出,迅速抽枝展叶,叶片浮现文字:
>“有个孩子每天来这里刻字。
>他已经刻了一百零三次。
>他说,总有一天会有人看见。”
秃毛鸡咕哝道:“这年头连草木都在搞革命了。”
抵达西北当日,沙暴再起。狂风卷着黄沙扑向兵俑阵,天地混沌。少年立于阵前,取出断笛欲再度吹奏,却被一股无形之力阻住。他心头一震??这不是外力压制,而是忆辉自身在抗拒。
“等等。”秃毛鸡眯眼望向第一排陶俑,“你看它的眼睛。”
少年凝神望去,只见原本模糊的眼眶中,竟渐渐浮现出清晰瞳孔,如同被某种力量重新雕刻。紧接着,那尊陶俑缓缓抬起右手,指向自己胸口??那里泥封尚未完全剥落,但裂缝间赫然露出一角布料,竟是军中文书官才有的青灰袖衬。
“他是记录者!”少年猛然醒悟,“他还记得一切!”
就在此时,整支军队同时动作??三千只手齐齐拍向胸膛。泥块崩裂,尘烟四起。一道低沉、破碎、仿佛从地底深处挤出的声音终于响起:
“我……记……录……”
一个字,用了整整十年才吐出。
第二个字紧随其后:“下……了……”
第三个字带着血沫般的杂音:“真……相……”
少年跪倒在地,泪流满面。这不是哭声,这是陈述!是沉默千年后的第一句证词!
他颤抖着打开随身携带的《缄言录》空白附册,咬破指尖以血为墨,开始疾书:
>“北征败军实情如下:
>天启十二年冬,北境战事吃紧,前线尚有存粮五日、箭矢充足,士卒皆愿死战。然朝廷密令下达:‘不准撤退,不准报败,不准生还’。理由为‘恐动摇国本’。
>将军拒签军令,当夜遭毒杀。副将被迫执掌大军,率部硬攻敌营,全军覆没八成。残部突围归国,却被诬为‘临阵脱逃’,押解至此施行‘失语葬’。
>其中三百二十七名士兵曾在临刑前写下遗书,藏于铠甲夹层,今已随陶俑出土,内容均为家书、忏悔与控诉。
>执行官员贺元德(即青年之父)曾私下焚香祷告:‘吾非无情,然上有高堂,下有幼子,若违令,则全家俱灭。’
>此案非一人之罪,乃制度之恶。它教会我们:当权力恐惧声音,便会先杀死语言本身。”
写毕,他将血书置于阵前。风沙骤停,三千陶俑齐齐低头,似在阅读,又似在默诵。
三天后,考古队清理出第一批铠甲遗物,果然在夹层中发现大量残信。一封写着:“娘,我不是逃兵,我是被逼回来送死的”;另一封是年轻士兵写给未婚妻的:“你说等我回来成亲,可我现在连名字都没有了”;还有一封用炭笔潦草写就:“如果将来有人看到这封信,请告诉世人,我们曾经存在过。”
全国震动。
民间呼声高涨,要求彻查“失语葬”背后整个权力链条。连一向保守的太学院都召开辩论会,主题为:“沉默是否也是一种暴力?”
少年受邀出席,面对满堂儒生,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读过的每一本经典,都是幸存者写的。可那些没能留下文字的人呢?他们的思想、爱恨、梦想,难道就不配被称为‘历史’?”
无人反驳。
会议结束后,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学究拄拐走到他面前,颤声道:“我年轻时……参与编修国史……删去过一段关于‘哑疫村’的记载……当时觉得……不过是几个贱民罢了……现在……我睡不着了……”
少年握住他的手:“那就说出来。不是为了求饶,是为了让后来人知道,一个人是如何一步步变成帮凶的。”
老人当场嚎啕大哭。
一个月后,这位老学究主动前往“犹豫堂”,在一面空白墙上亲手写下自己的忏悔录,并附上当年删改史料的具体细节。此举引发连锁反应,十余名曾参与掩盖历史的文官相继公开认罪,其中三人选择终身禁言,以示赎罪。
而此时,东海上又传来新消息:那群海豚消失了,但在它们最后出现的地方,海底升起一座珊瑚礁,形状酷似一本打开的书。潜水者冒险探查,发现礁石缝隙中嵌着一块金属牌,上面镌刻着一段话:
>“我们曾是渔夫的儿子、女儿、妻子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