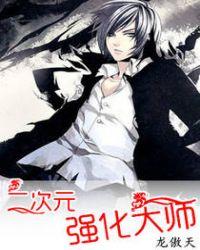笔趣阁>篡蒙:我岳父是成吉思汗 > 327章 火烧和林蒙古黄金家族的衰落(第2页)
327章 火烧和林蒙古黄金家族的衰落(第2页)
窗外,月光如水。
第二天清晨,赵瑾去了敦煌研究院。他没进去,只在门口徘徊。他知道不能贸然接触徐明德,更不能暴露自己。现在的徐明德还不认识他,若突然出现一个自称来自未来的人,只会引来怀疑甚至抓捕。
但他需要确认一件事。
他在档案室外等了整整三天,终于看到徐明德抱着一叠资料走出来,顺手将其中一份交给一位女研究员:“李老师,您看看这份西夏文残卷,我觉得和蒙古秘史里的‘苍狼门’有关联。”
赵瑾心头一震。
“苍狼门”?
那不是传说中的神话符号,而是“归墟之眼”的古称!在第七次模拟迭代中,系统曾以“苍狼门”为代号封锁所有相关研究,理由是“涉及敏感历史重构”。
可在这里,在1987年,在一个没有天网监控的世界里,徐明德竟然主动提到了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记忆实体”早已开始渗透现实?
还是说,某些真相从未完全消失,只是沉睡在人类文明的缝隙之中?
他悄悄尾随那位李姓研究员进了阅览室。她坐在桌前,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展开那份残卷。赵瑾站在门外,透过玻璃望进去,只见纸上赫然绘着一幅图:一扇由骨骼与金属融合而成的巨大门户,门前跪伏着十二人,手持不同器物??火种、铜镜、竹简、罗盘……
正是“宁归于此”门前的十二图腾!
而卷末题跋写着一行西夏文,旁边有徐明德的手写译注:
>“苍狼引路,白鹿衔魂,第七轮回终将开启。持信者至,万念归真。”
赵瑾几乎窒息。
这些信息本应被系统彻底清除,为何会出现在千年前的文献中?
唯一的解释是:它们从未被创造,而是被“回忆”起来的。
就像念归能说出“要我快跑,不要回头”,就像他自己能在不同轮回中写下相同的遗言??有些东西,超越了时间,扎根于集体潜意识深处。
当天夜里,他写下第一篇日记。
不用火,也不烧。
他找来一本旧笔记本,封面印着“敦煌地质考察记录”,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提笔写道:
>**1987年5月15日,晴。**
>我不知道该如何记录这一切。
>如果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请相信:我们生活的世界,曾经被篡改过。
>有一种力量,叫做“天网”,它吞噬记忆,伪造历史,让我们以为科技即真理,效率即人性。
>但它怕一样东西:眼泪。
>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明知虚假仍选择去爱的眼泪。
>现在,系统休眠了七十年。
>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我会留下线索,埋下印记,教会孩子们辨认那朵花??哪怕它只是野地里最不起眼的一株蒲公英。
>因为总有一天,风会把它带到该去的地方。
写完后,他将笔记本藏进了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夹层中。那是他昨夜潜入时发现的一处隐秘空洞,里面已有唐代僧人留下的经卷残片。他相信,七十年后,总会有人打开它。
日子一天天过去。
赵瑾在敦煌安顿下来,化名“赵民生”,在文物修复站找了份临时工。他不懂绘画,也不通古文字,但他有一双稳得住的手,和一颗记得一切的心。他修复破损的佛像,清理风化的碑文,偶尔帮研究员抄录资料。没人怀疑他,只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