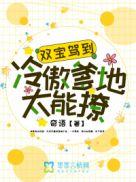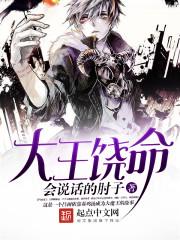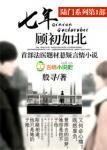笔趣阁>秦人的悠闲生活 > 第三百零九章 苦酒(第3页)
第三百零九章 苦酒(第3页)
老农叹道:“我们不怕官,就怕官换了还是一个样。只要别再抽丁去修陵、去戍边……咱就烧高香了。”
刘肥默然。他知道,百姓所求不多,不过是安稳二字。而帝王口中宏大的“变革”,落到民间,不过是一碗饭、一亩田、一夜安眠。
回到太学,刘肥伏案疾书,将沿途见闻录于竹简,题为《新政纪行》。他在末尾写道:
>“政不在高,而在落地;法不在严,而在惠民。陛下欲改苛法,非因怯于天下,实因听见了泥土中的哭声。这声音,藏在每一粒稻谷里,每一滴汗水中,每一个母亲哄孩子入睡时的歌谣里。”
夜深,他再次翻开公子高手稿,轻轻添上一笔:
>“老师曾言:历史是失败者的哀鸣。今日我补一句:改革,是生者的希望。”
数月过去,边关渐稳。蒙恬以雷霆之势击退匈奴,斩首三千,俘获牛羊无数,单于再度遣使求和。与此同时,新政全面铺开:关中水利渐成,渭北荒田变良田;乡老会初试成效,多地贪吏被揭发罢免;太学府百家争鸣,墨家讲“兼爱”,道家论“无为”,竟无人阻拦。
然而,暗流从未停止。
冬至之日,嬴政在咸阳宫举行大祭。百官齐聚,祭祀天地祖先。仪式将毕,忽有刺客自神庙梁上跃下,手持短刃直扑御座!千钧一发之际,蒙毅挺身挡刃,肩胛中伤。禁军迅速围杀刺客,当场格毙。
经查,刺客乃赵高旧仆,藏身宫中已逾三月。赵高被下狱审讯,但他咬定不知情,称“必有奸人栽赃”。
李斯主审,连审七日,终从其家奴口中撬出真相:赵高勾结宗室赢腾,意图趁新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拥立傀儡,恢复严法。
嬴政冷眼听完供词,只说一句:“车裂,夷三族。”
诏下之日,咸阳震动。赵高一族尽数伏诛,牵连者三百余人。赢腾自尽于府中,头颅悬于城门三日。
血雨腥风过后,朝堂为之一清。
次年春,嬴政登临咸阳南郊观耕台,亲执耒耜,象征性耕田三垄。百姓欢呼雷动。礼毕,他当众宣读《仁政诏》:
>“朕承天命,统六合,然省己过,知苛政伤民,峻法累世。今革故鼎新,宽徭薄赋,与民休息。愿我秦人,耕有田,居有屋,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此非朕之恩,乃天下共治之果也。”
诏书传遍四方,万民感泣。
刘肥站在人群中,望着那苍老却挺拔的身影,忽然明白??所谓悠闲生活,不是没有纷争,而是明知艰难,仍选择向善而行。
三年后,嬴政病重。临终前,召刘肥入宫。
“《列国史》……你一直讲得很好。”嬴政躺在榻上,气息微弱,“朕死后,你要继续教下去。告诉后来者,强国不易,守成更难。唯有不忘百姓,方得长久。”
刘肥含泪叩首:“臣必终身奉行。”
嬴政闭目,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高儿……朕没辜负你。”
当夜,嬴政崩于咸阳宫,享年七十三岁。举国哀悼,四海同悲。
安文继位,是为秦二世。他遵父遗诏,延续新政,重用李斯、刘肥等人,天下太平,史称“延康之治”。
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刘肥拄杖立于骊山书院门前,看学子们诵读《列国史》,笑声朗朗。他仰望苍穹,轻声道:
>“老师,您看见了吗?炊烟依旧袅袅,鸡犬依旧相闻。秦人的悠闲生活,终于来了。”
风过林梢,仿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