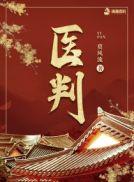笔趣阁>秦人的悠闲生活 > 第三百一十九章 各奔东西(第2页)
第三百一十九章 各奔东西(第2页)
殿内霎时寂静如死。
少府监赵高颤声劝谏:“陛下……此举恐致国库空虚,若匈奴南下,军饷何来?”
嬴政冷冷瞥他一眼:“若百姓饿死,还要军队何用?传旨下去,少府即刻调拨黄金五百斤、铜钱百万枚,用于采购外地粮食补仓。另命韩信从河西抽调两千骑兵,护送粮队入关,沿途若有盗匪劫掠,格杀勿论!”
众人再不敢言。
退朝之后,靳思独自走出宫门,寒风扑面,却觉胸中滚烫。他知道,这一局棋,嬴政走得很险??大规模放粮,等于向天下宣告朝廷仍有余力,既能安抚民心,又能震慑潜在叛乱者。更重要的是,此举将彻底打破李斯一党对财政的垄断,重新树立皇帝权威。
然而,危险也随之而来。
当晚,靳思回到府邸,刚坐下饮茶,家仆匆匆来报:“门外有一蒙面人求见,自称来自琅琊。”
靳思皱眉,命人带入。那人全身裹在黑袍之中,摘下面巾,竟是王离贴身亲兵。
“将军!”士兵扑通跪下,声音哽咽,“王大人命我星夜赶来,有紧急军情禀报!”
“讲。”
“琅琊近日发现齐国旧贵族密会,暗中联络楚、魏遗族,意图拥立田氏后裔复国。更可怕的是……他们已在民间散播谣言,称‘新帝弑兄夺位,扶苏冤魂夜哭骊山’,百姓已有动摇之势!”
靳思瞳孔骤缩。
这不仅是叛乱前兆,更是精心策划的心理战??利用扶苏之死,挑动民众对朝廷的不信任。若处理不当,一场席卷东方的大乱或将爆发。
他立即提笔拟信,命快马送往咸阳,请嬴政速决对策。同时,他又修书一封,寄往祁连雪山下的韩信营中,请求派遣精锐骑兵南下布防。
三日后,嬴政回信抵达,仅有八字:“卿可便宜行事,朕信汝。”
靳思握信良久,终是长叹一声。他知道,自己已被推上风口浪尖。既是皇帝信任的臂膀,也成为众矢之的。但他更清楚,若此刻退缩,扶苏一生为之奋斗的秩序,将毁于一旦。
于是,他召集亲信幕僚,制定三策:一、在关中各县广设“忠义讲堂”,由识字吏员宣讲扶苏生前政绩与仁德,澄清谣言;二、联合萧何,在放粮过程中严查贪腐,凡克扣救济粮者,不论官阶,一律斩首示众;三、秘密启用秦廷旧部,潜入东方诸郡,搜集叛乱证据,伺机反制。
与此同时,他亲赴潼关,会见正在读书的公子衡。少年已初具风骨,见靳思到来,恭敬行礼。
“先生为何而来?”衡问。
靳思凝视着他,缓缓道:“因为你父亲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将来治国者,必是衡也。’”
衡闻言怔住,眼眶渐红。
“你可知当今局势?”靳思继续道,“有人想让你祖父怀疑你父亲,想让天下人忘记你父亲做过的一切。但他们忘了,真正的功业,不会因死亡而消失。”
“那我该做什么?”衡坚定问道。
“读书,明理,等时机。”靳思轻抚其肩,“等到你能站上廷议大殿那一天,你要让所有人听见,扶苏的儿子,是如何继承他的意志的。”
风雪依旧,但关中的土地深处,已有春意悄然萌动。
数月后,随着放粮政策全面落实,饥民得救,流言渐息。萧何在奏章中写道:“今岁虽灾,然百姓感念圣恩,街头巷尾皆传‘陛下仁孝,不负先太子遗志’。”
而就在这一年夏末,一名来自齐地的商人被捕,搜出身上的密信赫然写着:“七月十五,举火于泰山,天下响应。”
靳思手持密信,立于咸阳城楼,眺望东方。
他知道,风暴尚未结束。
但只要人心未冷,火种犹存,秦人的悠闲生活,终将在废墟之上,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