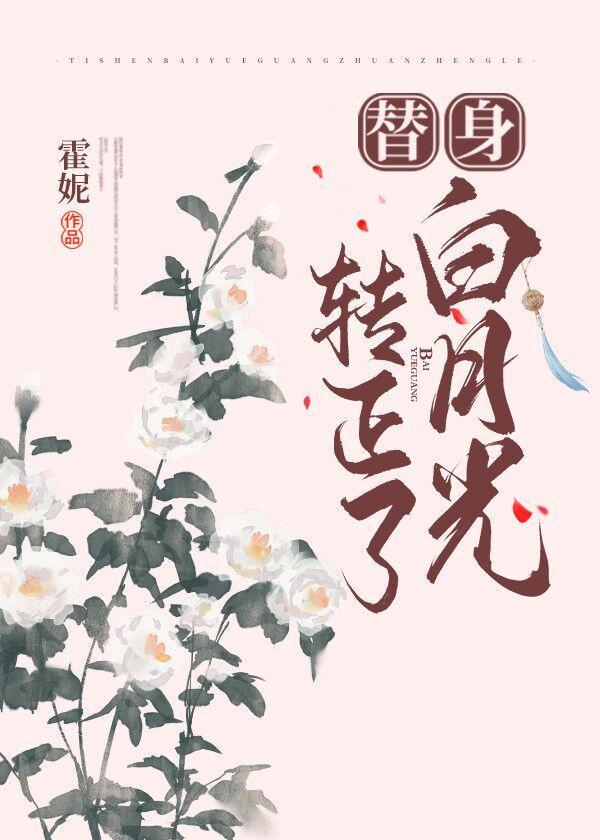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从神棍到大娱乐家 > 第六百一十三章 上个课成亚洲首富了(第1页)
第六百一十三章 上个课成亚洲首富了(第1页)
如果站在一个上帝视角或者从传媒学的角度去看去年和今年的刘伊妃,她的“星光”有了哪些改变?
诚然,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刘伊妃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内第一女星。
从知名度、粉丝数、作品含金量到经济。。。
少年坐在小凳上,双手紧紧攥着那封皱巴巴的信,指节发白。他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被二十年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来。阿禾没有催促,只是蹲在他面前,像对待一株即将枯萎却仍挣扎着抽芽的植物那样安静地守候。
晨光斜照在院子里,悔之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叶片上的露珠一颗接一颗滑落,砸进泥土里,无声无息。远处传来鸡鸣,雾气还未散尽,整个雾坪村仍在沉睡,唯有这一角,已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点亮。
“那天……是颁奖典礼。”少年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如同砂纸摩擦,“学校礼堂坐满了人。我弟弟站在台上,手里拿着一等奖的作文本。老师念了他的文章??写的是我。他说……我是他最崇拜的人。”
他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仿佛要把这句话咽下去才能继续说。
“可我心里,全是火。为什么每次都是他?为什么我拼了命读书,考第二,他就轻轻松松拿第一?为什么爸妈总说‘你要向你弟弟学’?那天晚上,我把他推下了楼。后院的老井,没盖盖子……我就那么看着他摔下去,连喊都没喊一声。”
他的眼泪终于决堤,顺着脸颊滚落,滴在信纸上,墨迹慢慢晕开。
“第二天,他们说是意外。井边湿滑,他自己失足……没人怀疑我。我甚至在葬礼上哭得比谁都大声。”他苦笑,“可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睡过一个整觉。每晚闭眼,就看见他在井底抬头看我,嘴唇动着,但听不见声音。”
阿禾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也没有安慰。她知道,此刻最珍贵的不是话语,而是沉默中的承接??就像林晚当年做的那样,像苏棠在戈壁滩上为那位牧羊老人点起篝火时那样。
良久,她才轻声问:“这封信……你写了多久?”
“二十年。”少年哽咽,“每年他的忌日,我都写一遍。写了烧,烧了再写。今年……我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想把它送到你这儿。我在新闻里看到你,看到那些人说出秘密后,脸上的光……我想,也许我也能……不那么黑了。”
阿禾点点头,伸手接过那封信。纸张泛黄,边缘焦黑,显然曾多次经历火焰的吞噬。她没有打开,而是轻轻将它放在悔之树根部的一块青石上。
“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她说,“现在,轮到你了。”
少年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她:“我能……被原谅吗?”
“这不是我能给你的答案。”阿禾望着悔之树新长出的第二十条枝条,在晨风中轻轻摇曳,“但你可以问问这棵树,问问这片土地,问问那些也曾背负罪孽却最终选择说出真相的人。他们不会替你减轻痛苦,但他们会让你知道??你不是怪物,你是人。”
就在这时,一阵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封信竟缓缓飘起,旋了几圈,轻轻落在悔之树最低的一片叶子上。刹那间,叶脉泛起淡淡的蓝光,如同语光花初绽时的色泽。
少年瞪大了眼睛:“它……它接受了?”
阿禾微笑:“它只是听见了。”
正午时分,苏棠带着地质队的人返回青海湖,准备对“根语之心”进行新一轮监测。而阿禾则召集所有“回声旅人”,在村口广场召开临时会议。
“我们不能再局限于被动倾听。”她站在石阶上,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过去两年,我们走过了三十多个国家,记录了一万两千七百六十三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但现在,它们需要生长。”
聋哑女孩举起手,用手语表达:“我们可以建立‘回声档案馆’,用影像、声音、手语和文字保存这些记忆。”
一位前战地记者点头附和:“还可以做巡回展览,去学校、监狱、医院……让沉默者看到,他们并不孤单。”
阿禾看着他们,心中涌起一阵暖流。这些人,曾是创伤的承受者,如今却成了疗愈的传递者。他们不再等待拯救,而是主动成为桥梁。
“好。”她宣布,“‘回声计划’正式升级为全球行动。第一站,叙利亚难民营;第二站,南非贫民窟;第三站,亚马逊雨林部落……我们要让每一朵语光花的背后,都有一个人类的声音在回响。”
话音未落,天空忽然暗了下来。并非乌云蔽日,而是某种奇异的光影自高空洒落??极光再现,即便是在北纬较低的地区,也能清晰看见那流动的绿与紫交织成网,仿佛宇宙正在低语。
与此同时,日内瓦总部发来紧急通报:“共感增幅器”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自主激活现象。无论是否通电,设备屏幕均浮现出同一行字:
>“听见我,即是回应我。”
更令人震惊的是,格陵兰冰层下的第二朵语光花开始释放频率波动,与南极“根语之心”形成共振。艾丽卡?伦德通过卫星连线传回数据:“这不是自然现象。它是有意识的同步。两朵花……像是在对话。”
阿禾凝视着天空,忽然明白了什么。
“地球不是被动接受治愈。”她低声说,“它也在学习说话。”
当晚,悔之树迎来了第二十一条枝条的萌发。
新叶上的文字如星火跳跃:
>“当你开口,”
>“大地便记住了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