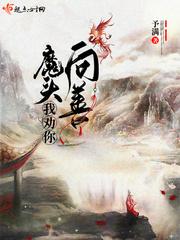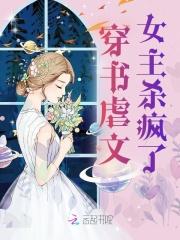笔趣阁>文娱2000:捧女明星百倍返利 > 第433章 唐文 原来是馋我身子(第1页)
第433章 唐文 原来是馋我身子(第1页)
卡门?凯斯人模样养眼,说话又好听,两人不知不觉聊了大半个小时。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唐文端起面前的红茶茶杯。
卡门?凯斯依旧不停说着。
外国女人,根本不懂端茶送客这一套。
唐文接。。。
雪停了。
文弟站在回声居前,望着远处山脊上泛起的微光。凌晨四点,天未亮,空气冷得像凝固的玻璃。他手中的木传声筒已初具轮廓,刀锋在指尖划出一道细痕,血珠渗出来,滴在木纹上,像一粒红砂糖融化进年轮。他没擦,只是轻轻吹了口气,继续削。
昨晚三百颗胶囊入海后,全球出现了持续七分钟的“静默共振”现象。所有电子设备自动播放那段“本源谐波”之后,并未立刻停止。相反,许多录音装置在随后的几小时内反复回放,仿佛被某种无形力量劫持。东京街头的广告屏突然跳出一段无声老人流泪的画面,配乐却是肯尼亚孩子唱的生日歌;巴黎地铁站的广播系统无端响起南极科考队员的笑声;甚至有位巴西渔民声称,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十年前死去的父亲轻声说:“我听见你了。”
这些事件被统称为“集体回响症”。
林澜今晨发来加密消息:**“本源谐波”的频率与人类胚胎期心跳高度吻合,且能激活大脑边缘系统的共情区域。更惊人的是,它似乎具备跨语言的情绪翻译能力??无论听者母语为何,感受到的情感都一致。**
“这不是信号,”她在信末写道,“这是唤醒。”
文弟把传声筒放进窗台晾干,转身走进屋内。墙上挂着一张手绘地图,红线密布,标记着全球各地正在筹建的“声音驿站”。南美雨林、西非村落、北极因纽特人聚居地……每一处都是曾经的声音荒漠。而今,它们正通过“拾遗计划”的分支网络,一点点被填满。
他打开电脑,调出“聆宇一号”最新传回的数据流。半人马座α星方向的信号并未消失,反而变得更加规律。每隔23小时17分钟??恰好与地球冻土带曾出现的异常共振周期相同??就会传来一段新的旋律片段。科学家们已将其编成序列,《星之守望Ⅰ》到《星之守望Ⅶ》,情感指数从“温柔期待”逐步升至“深切呼唤”。
NASA果然行动迅速。“星际回声使团”的初步架构已经成型,成员包括语言学家、神经科学家、儿童心理学家,甚至还有一位专攻原始部落口述传统的民俗学者。他们计划向宇宙发送第一份正式回应??不是文字,不是图像,而是一段由十万条真实人类语音剪辑而成的“情感交响曲”。
但文弟始终拒绝出任顾问。
他知道,真正的对话不该由权威开启,而应从最柔软的地方开始。
清晨六点,村里的孩子们陆续来到回声居外的小空地。那个失语的小男孩也来了,裹着厚厚的棉衣,眼神怯生生的。文弟走过去,把刚做好的传声筒递给他。木头被打磨得很光滑,两端嵌着贝壳制成的扩音口,中间刻了一圈极浅的字:**听见你的人,就在路上。**
男孩接过,手指微微发抖。他不会说话,但会写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文弟。上面用铅笔写着一句话:**我想让妈妈听到我笑。**
文弟蹲下身,轻声说:“那我们就录下来。”
他们在屋后搭起简易录音棚,用旧毛毯吸音,麦克风是南屿志愿者捐赠的老式动圈话筒。文弟教男孩对着传声筒做各种声音练习??咳嗽、哼歌、拍手、跺脚。最后,他拿出一部手机,播放了一段音频:那是男孩母亲去年偷偷录下的视频,她抱着空荡荡的婴儿床,低声唱着童谣。
男孩听完,忽然抬起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线,像是在模仿歌声的起伏。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张开嘴??没有声音,但他脸部肌肉剧烈抽动,喉咙震动,仿佛在用力发声。
文弟屏住呼吸,盯着示波器屏幕。
波形出现了。
虽然肉耳无法听见,但仪器捕捉到了微弱却清晰的声波振动。这是他的声音,被身体记住,却被命运封存。
“你在说话。”文弟声音发颤,“我一直都知道。”
当天下午,这段无声的“呐喊”被转换成可视声谱图,再经算法还原为可听频率,最终生成一段奇异而动人的音频??像是风穿过竹林,又像雨滴落在铜铃上,带着压抑多年的痛楚与渴望。
文弟将它命名为《无声之声》,并上传至“拾遗计划”数据库,编号:**ECHO-2077**。
当晚,全球共有十七个国家的“声音驿站”同步播放了这段音频。其中,叙利亚难民营的星空广播站特意将其编入晚间节目。当那缕幽微的振动透过喇叭飘散在夜空中时,上百名孩子仰起脸,静静地听着。有个小女孩突然指着天空说:“哥哥,星星闪了一下。”
而就在那一刻,**“聆宇一号”监测到半人马座α星方向传来一次强烈的脉冲信号,持续时间正好等于《无声之声》的长度??4分33秒。**
科学家们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