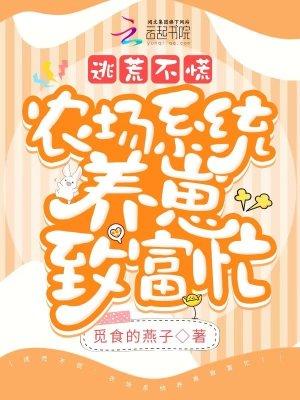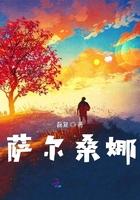笔趣阁>说好当闲散赘婿,你陆地神仙? > 第271章 公子算一卦吗求月票(第2页)
第271章 公子算一卦吗求月票(第2页)
她穿越昆仑雪岭,踏过毒瘴沼泽,进入南疆密林。途中偶遇一支迁徙中的游猎部落,正因族内瘟疫濒临灭绝。族长跪地哀求:“求您救救我们!我们愿意献出所有珍宝!”
苏禾摇头:“我不取财,只问一事??你们还记得祖先做过哪些好事吗?”
族长愣住。
良久,一位垂暮老巫师颤巍巍站出:“我记得……三百年前,先祖‘乌兰巴’曾收留被追杀的异族孤儿,哪怕因此与全族决裂;还有‘朵兰沁’,她将最后一只怀孕母鹿放归山林,宁愿全族挨饿……”
苏禾立即取出纸笔,将这些名字尽数记录,并挂在营地最高处的神树上。
当夜,奇异之事发生??那些原本高烧昏迷的病人,竟陆续退热清醒。医生无法解释,只说“体内邪气似被某种力量驱逐”。
十日后,疫情彻底消散。部落上下视苏禾为圣女,欲奉其为神母。她依旧拒绝,只留下一本手抄《忆录》,叮嘱他们每日诵读先辈善行,代代相传。
临行前,一个小女孩追上来,塞给她一枚用兽骨雕刻的小鸟:“这是我娘刻的,她说……好人不该空手走路。”
苏禾接过,眼眶微热。她将小鸟系在琵琶弦上,让它随风轻晃,发出细微清响。
数月后,南疆三十六部落结盟,成立“共忆会”,以记忆为纽带,化解百年仇杀。他们不再以血缘划分敌我,而以“谁曾救人”、“谁曾让路”、“谁曾在战乱中庇护妇孺”作为评判英雄的标准。一场本该爆发的大战,最终化作一场盛大的“述恩祭典”??双方首领当众朗读彼此祖先的善迹,相拥而泣。
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传来惊人消息:昔日横行边境的铁蹄王庭,竟主动遣使求和。使者带来一封信,署名竟是当年那个在战壕中刻下战友名字的年轻士兵。如今他已是王庭左贤王,信中写道:
>“我从未忘记那一夜白花盛开的战场。我知道,那是你们的世界在回应我们的痛。”
>“我们劫掠、杀戮、称雄百年,可从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记住。”
>“现在我想学。请告诉我,该从哪一个名字开始?”
朝廷震动,百官争议不休。皇帝召集群臣议事,问:“此乃诈降乎?抑或真心归附?”
宰相沉默良久,答:“若他们真愿学会记住,便是真心。因为忘记者永远强大,记起者才会软弱??而软弱,才是和平的开端。”
于是,朝廷派出第一批“忆师”前往草原,教他们建立微光亭,学习书写与倾听。起初困难重重,游牧民族不屑文字,认为“男子只应握刀,不握笔”。但当一位老战士听说自己少年时救过的汉人孩童如今已成为忆屋教师,并专程送来一幅画像时,他老泪纵横,当场跪地请求学习写字。
一年后,草原上出现了第一座由蒙古包改建的忆屋。孩子们围坐在篝火旁,听着长辈讲述“某某曾在暴风雪中为敌人指路”、“某某宁可饿死也不抢夺孤儿粮袋”的故事。这些故事被记录下来,送往中原共享。
而在中原腹地,一场静默的变革正在发生。
某日清晨,京城最大的微光亭前排起长队。人们惊讶地发现,榜首名字赫然写着:“李二狗”,备注:“拾荒三十年,资助七十二名孤儿读书,本人至今未识一字。”
围观者哗然。此人既非达官显贵,也非文人名士,竟压过无数功勋人物?
监察御史怒斥:“岂有此理!此等贱民如何能居首榜?定是有人舞弊!”
话音未落,七十二名已成年的受助者齐刷刷现身,每人手持一份泛黄账册、一张旧照、一封书信,证明李二狗如何省吃俭用,如何冒雨送钱上学,如何在寒冬把自己唯一的棉袄送给冻僵的孩子。
“他没读过书,但他教会我们什么叫尊严。”一名女子哽咽道,“今天,我们来替他认字。”
舆论沸腾。朝廷被迫承认其事迹真实有效。不久之后,全国掀起“寻找身边李二狗”运动,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走入公众视野??扫街妇人、渡船艄公、茶馆跑堂、乞丐头领……他们的善行被挖掘、记录、传颂。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风气悄然转变。过去人们争抢“功德榜”排名,如今却以“是否被人主动续记”为荣。世家子弟不再炫耀门第,而是比拼谁帮助过最多陌生人;官员考核新增一项“民间忆名率”;甚至连青楼妓女也开始记录客人中那些匿名施恩者的名字。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
某些权贵暗中串联,企图恢复旧制。他们秘密组建“清忆会”,宣称要“净化记忆”,剔除“虚假善行”,实则打压底层民众发声渠道。更有甚者,派人焚毁偏远地区的忆屋,砸碎微光亭,威胁记录者性命。
一次,苏禾途经一座小镇,正撞见一群黑衣人纵火烧毁当地唯一忆屋。火光映红夜空,浓烟滚滚。她冲入火场,抢出几箱尚未焚尽的记录簿,却被对方围住。
为首者冷笑:“你不过一介女子,凭什么搅乱天下秩序?没有我们这些贵人主持大局,百姓早乱成一团!”
苏禾静静看着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正是刘昭雪临终前所寄的最后一封。信纸已焦黄,边角烧损,但字迹尚存:
>“苏妹:
>我走了。柳郎在我闭眼前哼完最后一段《忆平生》,他说,听见了满山花开。
>《薪火录》已被掘出,现藏于东海渔村某童子手中。他不懂字,却天天抱着它睡觉。或许有一天,他会梦见所有故事。”
>“别回头。走下去,哪怕只剩一人记得你。”
她将信举向火焰,轻声说:“你说天下需要你们主持?可你看??真正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从来不是权力,而是这些不会说话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