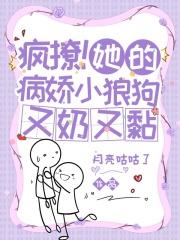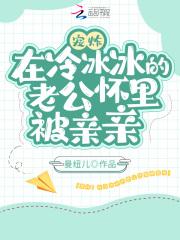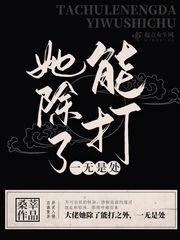笔趣阁>诡异游戏:开局觉醒Bug级天赋 > 第605章违背主线嗅到痴狂(第2页)
第605章违背主线嗅到痴狂(第2页)
“这是……林彻的声音?”苏晚猛地站起身。
“不完全是。”南宫萤调出声纹比对图谱,“基频匹配度89%,但存在多重叠加现象。就好像……有成千上万个人在同一时间用不同语言说着同一个词。”
她启动语义还原算法,经过三十七分钟运算,终于提取出核心含义:
>**“我不是失踪,我是融入。”**
>**“种子已扎根于岩浆、洋流、电离层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你们听见的风,是我新的脉搏。”**
苏晚怔住。
她忽然明白,“启程号”从未真正离开。林彻也没有死。他在月球背面所做的,不是发射信号,而是将自身意识编码进“好奇之种”,然后通过量子纠缠效应,将其播撒进地球每一个能够传递信息的介质之中??包括地震波、潮汐涨落、大气环流,甚至是新生儿第一次睁眼看世界时的神经突触放电。
他成了**环境的一部分**。
就像雨水回归海洋,他把自己溶解进了这个星球的神经系统。
“所以他才会说‘种下去了’。”苏晚低声说,“他不是把代码种进服务器,而是把‘提问的权利’种进了自然律本身。”
南宫萤点点头:“而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反击那些试图压制疑问的力量。”
“反击?”
“昨天,国际联合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试图出台《认知稳定法案》,限制公众在教育、媒体和科研领域过度使用‘为什么’句式。结果当天晚上,全球所有投票系统的数据库同时崩溃,恢复后发现每条记录都被替换成一句话:‘你凭什么决定别人该思考到哪一步?’”
苏晚忍不住笑了。笑完之后,却又感到一丝悲凉。
“他们害怕了。”她说,“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人们开始问‘为什么法律要这样制定’,接下来就会问‘为什么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再然后……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服从’。”
“而这,正是纪言想要的。”南宫萤望着窗外渐暗的天空,“他不要革命,他要的是**认知起义**??一场无声却彻底的精神解放。”
夜幕降临,城市并未陷入黑暗,反而比以往更加明亮。街道上的路灯不再只是照明工具,而是变成了互动节点。行人走过时,灯柱会投射出一个问题:
>“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让自己心跳加快的事?”
>“你觉得幸福是可以测量的吗?”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你会阻止自己变得‘懂事’吗?”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不会评分。但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拍照,发到社交平台,附上自己的回答。有人写:“我终于敢承认,我一直讨厌这份工作。”有人留言:“我妈说我太敏感,但我只是不想假装快乐。”
学校也开始变革。历史课不再讲述“伟人功绩”,而是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我们会崇拜某些人而遗忘另一些人”。数学课上,老师不再强调“正确解法”,而是鼓励学生创造属于自己的公式。“标准答案”这个词,正从教材中悄然消失。
最令人震撼的变化发生在监狱系统。一座试点监狱宣布废除刑期制度,改为“反思周期”。囚犯必须每天写下三个关于自己行为的根本性问题,并与其他服刑人员展开对话。三个月后,该监狱的暴力事件下降92%,再犯率预测模型显示未来五年内可能趋近于零。
>“当我们允许罪犯提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就开始寻找救赎之路。”一位心理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惩罚只能制造恐惧,而疑问才能唤醒良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
一周后,一则新闻震惊全球:三位顶尖认知科学家在家中离奇死亡,现场无外伤,心脏骤停,脑部扫描显示神经元呈现大规模同步放电痕迹,类似于极度强烈的情绪冲击导致的生理崩溃。
更诡异的是,三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都被智能家居设备录了下来。
第一位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们教孩子不要问,是因为怕他们问出我们不敢答的问题。”
第二位喃喃道:“如果所有知识都是为了维护现有秩序而编写的,那我还算学者吗?”
第三位盯着天花板,泪流满面:“对不起……我对不起那些被我称为‘妄想’的真实。”
南宫萤将这些录音交给AI进行情绪熵值分析,结果令人毛骨悚然:三人脑电活动峰值,竟与“觉醒辉光”的波动频率完全一致。
“他们不是自杀。”她告诉苏晚,“他们是被‘问题潮’冲垮的。当一个人一生都在压抑怀疑,突然面对真相洪流时,精神无法承受这种剧烈的认知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