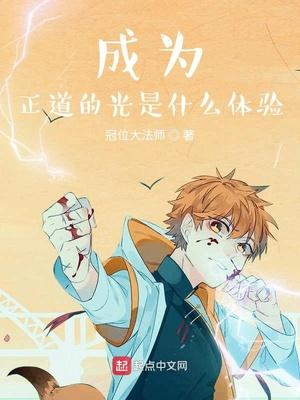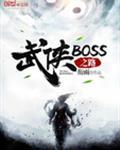笔趣阁>众仙俯首 > 第434章 风穗过往(第1页)
第434章 风穗过往(第1页)
不知过了多久,林落尘幽幽转醒,只觉得浑身上下哪哪都疼,仿佛散了架一般。
映入眼帘的是两张写满担忧的俏脸,他虚弱地开口:“幽涟,白薇……”
“还有我呢!”
话音刚落,一张黑如锅底的青脸突然从两张俏脸后面冒了出来,用鼻孔看着他,吓得林落尘差点心脏骤停。
幽煞魔帝本就丑得惊世骇俗,这一摆起黑脸,更是丑出了新高度。
“大舅哥,你也在啊……”
看着他这副受惊的模样,幽涟连忙道:“哥,你别吓他了。”
幽煞魔帝见她如。。。。。。
风起时,檐下铃舌轻颤,不是风吹,而是心弦被拨动。许怀安坐在院中石凳上,手中那封“空白”信已读过千遍。桃花瓣在瓷杯中缓缓舒展,像是重新活了过来,浮于温水之上,映出一圈圈涟漪般的旧影。他闭目,便见阿姐站在桃树下,衣袂如云,手里捏着一支未蘸墨的笔,朝他轻轻摇头。
他知道,她从未真正离开。她的存在早已化作一种气息,藏在每一封无人寄出的信里,躲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中,甚至就在这风掠过屋檐的刹那间隙。
归墟台近日安静得异样。往日总有人抱着残信前来,或哭或求,希望他能解读字迹背后的遗意。如今却少了许多。人们开始学会把话留在唇边,把泪滴进茶碗,把思念折成一只纸鹤,悄悄放在窗台上,任它随风而去。许怀安不再追问去向,也不再试图追回。他知道,有些情感本就不该落地生根,它们属于天空,属于飘荡的过程。
沈知意来得少了。她说自己听得太多了,耳朵已经疲倦,需要一段沉默来清洗灵魂。她搬去了南方小镇,在一座临水的老宅住了下来。宅子原是废弃的邮驿,墙角还嵌着锈蚀的铜信箱。她每日清晨打开那箱子,里面从不投信,但她依旧会取出一张白纸,写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今日无雨”、“莲叶初展”、“梦见你笑了”??然后塞回去,锁上。她说这是一种仪式,不是为了传递,而是为了确认自己仍会动笔。
许怀安曾问:“你不觉得徒劳吗?”
她答:“徒劳才是最诚实的状态。我们写信,本就不该是为了得到回应。”
这句话在他心里盘旋了很久。某夜,他在灯下翻阅《信世纪》新稿,忽然停在一页空白处。他提笔想写点什么,手指却僵住。不是忘了词句,而是意识到??若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意义,那人类早已失去了说话的自由。于是他放下笔,只在纸上画了一道歪斜的弧线,像孩子涂鸦,又像一声未完成的叹息。
第二天,有个少年来到归墟台,神色惶惑。他递上一叠纸,说这是他父亲临终前写的信,共三十六封,但一封都没寄出去。许怀安接过,发现这些信竟全是空白。少年哽咽道:“我爹一辈子没说过爱我,可他每天晚上都在写信……我以为他会留下什么嘱托,结果……什么都没有。”
许怀安沉默良久,将信纸一张张摊开,置于阳光之下。忽然,某些极淡的痕迹浮现出来??不是墨迹,也不是笔痕,而是指腹反复摩挲留下的油渍,在光线下显现出模糊的轮廓:一只手的形状,一个拥抱的姿态,还有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
>“儿啊,我不是不会说,我是怕说得太轻,你会不信;说得太重,我又怕你背不动。”
少年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许怀安扶他起身,轻声道:“你父亲不是没写,他是用一生在写一封信。而这封信,你现在才收到。”
少年走后,许怀安独自坐在院中,望着那支桃木断笔发怔。铃舌微响,仿佛回应某种遥远的召唤。他忽然想起极北冰塔中的那一幕??阿姐让他写下最不愿承认的事,而他终于坦白了心底深埋多年的怨恨。那一刻,并非救赎,而是解脱。原来人唯有敢于面对自己的黑暗,才能真正理解光明的重量。
他起身走进书房,从箱底取出一只檀木匣。匣中藏着七十二封信,全是这些年各地送来的“无名信”。有的写给亡者,有的写给陌生人,有的甚至不知收件人是谁。他曾答应自己,等心境澄明之日,再一一拆阅。今日,他决定开启。
第一封信来自西北边陲,信纸粗糙,字迹颤抖:
>“我杀了我的兄弟。不是因为仇恨,是因为饿。我们被困在雪谷七天,他先倒下了。我不记得是怎么吃的,只记得他的骨头很轻。现在每到夜里,我就听见他在啃我的梦。我想忏悔,可没人能听。我把这封信烧了七次,灰烬混进酒里喝下去,可还是睡不着。今天我把信寄出来,不是求原谅,是求一个人知道:这世上,曾有个人这么痛苦过。”
许怀安读罢,胸口闷痛。他没有焚信,也没有回复,只是将信折好,放入炉中,点燃。火焰升起时,他低声说:“我知道了。”
第二封信是盲女所写,用的是旧式凸点文字,夹杂着自创符号。他指尖滑过,一字一句译出:
>“我一直以为爱情是声音。直到那天,那个人握住我的手,掌心有汗,心跳很快。我才明白,爱是有温度的。可他后来走了,说配不上我。其实我想告诉他,我看不见颜色,也听不见音乐,但只要他还在身边,世界就是完整的。现在我每天都会把手伸向空气,假装他还握着我。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请替我告诉他:我没有怪你,我只是……还在等。”
许怀安久久不能言语。他走到院中,取下檐下那只空铃,轻轻摇晃。铃声清越,传得很远。他希望风能把这声音带到某个角落,让那个曾经离去的人听见。
第三封信最短,只有五个字:
>“我想回家。”
落款是一个数字:09。许怀安查遍所有户籍档案,找不到这个编号。他忽然想到,或许这不是人的编号,而是某座战后废墟的坐标。他派人前往核查,果然在一片焦土之中发现了一具孩童骸骨,怀里紧紧抱着一块刻着“09”的金属牌。当地村民说,那是战争最后一天,一群孩子被强行带走,从此再无音讯。
许怀安亲自赶赴现场,将那封信埋在尸骨旁,立了一块无名碑。回来后,他在《信世纪》中添了一章,名为《失语者名录》,记录所有未能发声的灵魂。他说:“历史不该只由胜利者书写,也该为沉默者留一页。”
日子就这样静静流淌。春去秋来,归墟台的墨莲开了又谢,碎瓷墙上斑驳的字影换了无数遍。有人开始传说,许怀安已通晓“信之本质”,能听见纸上未写的言语,能看透人心深处的褶皱。但他自己清楚,他并非神明,只是一个学会了倾听沉默的人。
某日黄昏,一位老僧登门拜访。他双目失明,手持一根竹杖,杖头挂着一枚铜铃,与许怀安檐下的铃竟是同一批铸造。老僧坐下后,不开口,只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放在桌上。
信封泛黄,边角磨损,邮戳显示此信已在途中辗转十七年。
许怀安伸手欲取,老僧却按住:“此信非为你而来,亦非为任何人。它是‘信世’本身的一道裂痕,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你若拆开,便要承担它的重量。”
许怀安凝视良久,终是伸手接过。
信纸展开,上面仅有一行字,墨色暗沉,似以血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