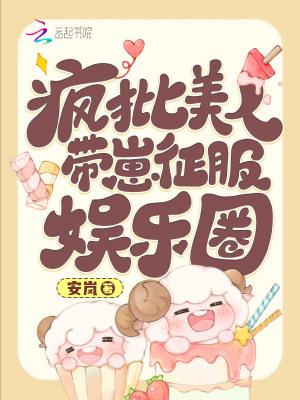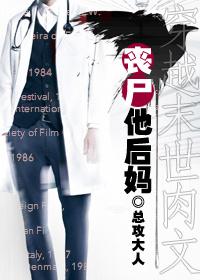笔趣阁>众仙俯首 > 第435章 天都异变(第2页)
第435章 天都异变(第2页)
“你叫什么名字?”他轻声问。
“我没有名字。”女孩摇头,“我娘说,等我把盒子交给正确的人,她就会给我一个名字。她说,名字也是一种信,只有当它被真正听见时,才算成立。”
许怀安沉默良久,终是点头:“我陪你去忆林。”
两人启程那日,天光未明。雪仍在下,细密如絮。他们乘舟渡海,船头燃着一盏孤灯,映照水面浮出层层叠叠的字影??全是过往被埋葬的信文,在寒夜里苏醒,随波流转。小女孩蹲在船沿,伸手触水,指尖划过“我想你”、“对不起”、“我还爱着你”等残句,嘴角竟浮起一丝笑意。
“它们在游动呢。”她说。
“是啊。”许怀安望着水底,“文字本就不该静止。它们该流动,该相遇,该彼此缠绕,像河流汇入大海。”
抵达忆林时,正值月圆。银白树林在夜色中泛着幽光,叶片上的文字如萤火般明灭。风起时,整片森林如同呼吸,低语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浩瀚的心潮。
他们走向林心。那里有一棵最为古老的树,树干粗逾十围,表面布满裂纹,形如掌纹交织。许怀安认得它??这是第一座信冢中最早生出的忆树,根系之下埋着最初十万封废信。
他挖坑,将铁皮盒放入,覆土,再以指尖轻抚树干,低声说:“收好了。”
刹那间,整片林子陷入寂静。连风都停了。随后,万千叶片同时震动,文字如星河倒悬,疯狂流转重组。一道光自地底升起,穿透树冠,直指苍穹。光柱之中,浮现一行巨大无比的字迹,横贯天际:
>“谢谢你,让我终于被读完。”
许怀安仰首,泪水滑落。他知道,这不是他的阿姐,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亡魂。这是所有未能发声者的集体回响,是“信世”对倾听者的致谢。
小女孩突然跪下,对着那棵树磕了三个头。起身时,她脸上已有泪痕,却带着释然的笑。
“我有名字了。”她说。
“是什么?”
“听见。”她轻声道,“我叫‘听见’。”
许怀安心中一震。这名字不是赋予,而是觉醒。唯有真正理解沉默重量的人,才能听见无声的呼喊;唯有走过漫长孤独的孩子,才配得上这个名字。
他牵她走出忆林。回程路上,谁都没有说话。但许怀安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就像春天不会突然降临,而是在冰雪深处悄然酝酿;“信世”的轮回亦非断裂,而是转化??从纸墨到心音,从传递到共鸣。
回到归墟台第三日,听见执意离去。她说她要去别的地方,把“听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许怀安没有挽留,只送她一支新制的竹笔,笔杆刻着两个小字:“未完”。
她走后,许怀安重拾《信世纪》手稿。他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提笔欲写,却又停下。这次,他不再追求意义,也不再试图总结。他只是任笔锋游走,画下一条蜿蜒的线,像河流,像血脉,像时间本身。
画毕,他合上书册,置于案头。窗外桃树上的那朵早春花已然凋谢,果实初结,青涩小巧,藏在叶间,不为人知。他忽然想起沈知意曾寄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终将在不说中相认。”
他笑了笑,吹熄灯火,躺下入睡。
梦中,他又见到了阿姐。这一次,她不再是桃树下的幻影,也不是雪中的背影。她坐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窗开着,风吹动桌上的白纸。她正低头写字,神情专注,嘴角微扬。
他站在门外不敢进去,直到她抬起头,望向他。
“你来了。”她说。
“我一直在找你。”他哽咽。
“可我从未离开。”她起身,走到门前,伸手抚过他的脸,“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你在读信的时候,我在;你在沉默的时候,我也在;甚至当你忘记我的时候,我还是在。”
“那你为什么不肯现身?”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