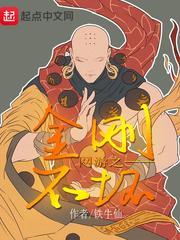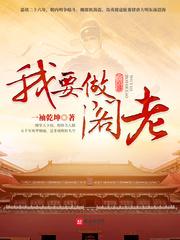笔趣阁>步步登阶 > 第527章 也不尽是坏人(第1页)
第527章 也不尽是坏人(第1页)
在帽子走后第一时间。
我便打了张君的电话,把有人过来捣乱的事情说了一遍,张君表现的也很平稳,在电话里说了一句知道了,他马上过来,便挂断了电话。
顾勇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我和张君的关系,另外他也不怎么怕,心想着他就带人在这里捣乱,也不动手,如果我对他动手的话,他先报警。
结果十几分钟不到的功夫。
顾勇发现不对劲了。
陆陆续续过来了七八辆车,每辆车上都下来了五六个人,甚至有的车下来了七八个人,也不知道车里面。。。。。。
列车驶过一片油菜花田,金黄的波浪在风中起伏,像大地终于学会了呼吸。陈宇靠在我肩上睡得安稳,手里还攥着那张他在海边捡来的贝壳。我轻轻抽出耳机线,把阿?的新歌调到循环播放。窗外阳光洒进来,照在他睫毛上微微颤动,像是某种无声的回应。
苏倩的消息又来了:“L-2信号复现,持续时间缩短至六分钟,但频率波形出现变异??叠加了儿童脑电α波特征。”
后面附了一条语音,她声音压得很低:“他们开始对目标人群做预适应训练了。不是直接控制,是让大脑先‘习惯’那种节奏……就像给耳朵套上隐形耳塞,慢慢听不见真实的声音。”
我盯着手机屏幕,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干扰器外壳上的刻字:“让声音回来。”
这不只是口号。它正在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认知游击战。
当晚我们住进三亚郊区一家民宿,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黎族妇女,说话带着浓重口音,却格外热情。她听说陈宇第一次看海,特意端来一碗温热的椰奶,说:“孩子喝了这个,夜里不会做噩梦。”
我道谢接过,却发现碗底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炭笔写着:“别信穿白大褂的医生。”
我的心猛地一紧。
这不是恶作剧。这种警告,在某些地方流传已久。育音谷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广,甚至渗进了民间口述记忆里,化作迷信、传说、老人吓唬孩子的睡前故事。而这些碎片,恰恰是最难被系统清除的部分。
第二天清晨,我趁陈宇还在熟睡,悄悄拨通赵岩的加密线路。接通后他只说了三个字:“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K-7还活着。”他说,“而且就在L-2。”
我屏住呼吸。
“巴西查封机构时,我们在设备底层日志里恢复出一段音频片段??一个成年男性反复念诵‘一级阶,闭嘴不哭’,语调机械,但有轻微口吃。经声纹比对,与档案中标记为‘K-7失语前最后录音’匹配度达91。3%。更重要的是,他的脑电活动显示残存语言中枢仍在尝试激活,只是长期受控导致输出路径断裂。”
“所以他一直在重复那些台阶?”我问。
“不止。”赵岩顿了顿,“他还自己加了一句:‘零级阶,忘了名字。’”
我愣住了。
一个人被剥夺语言到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的地步,却还能记住那套驯化程序……这是多么深的创伤?又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周振国知道吗?”我问。
“不知道。或者说,他已经不在乎了。对他而言,K-7只是数据点之一。但对我们来说……他是第一个受害者,也可能是唯一能反向破解核心算法的人。”
我望向窗外,晨雾未散,远处海面灰蒙蒙一片。如果K-7真的还活着,那他不仅是证人,更是钥匙。不是打开静默工程的钥匙,而是摧毁它的引信。
我决定改变行程。
原计划是送陈宇回家,然后独自前往南美。但现在不行。K-7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最快速度建立“幸存者网络”??让那些曾被沉默的孩子彼此看见、听见、确认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对抗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那种让人甘愿自我消音的心理机制。
我给许小阳发了条信息:“启动‘回声计划’。”
半小时后她回信:“已联络七省试点学校,十二名具备心理干预经验的教师志愿者待命。阿?同意担任声音疗愈顾问。问题是你能不能确保安全接入?”
我没有立刻回复。安全从来不是我们的前提,只是代价。
傍晚,我带陈宇去了海边公园。夕阳西下,几个孩子在放风筝,笑声随风飘荡。我坐在长椅上,打开笔记本,开始整理育音谷幸存者的线索。除了K-7,还有至少十九个编号儿童下落不明,其中三人曾在二十年前出现在云南边境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后来该校突发火灾,所有档案焚毁。
我正翻阅旧地图,忽然感觉有人站在身后。回头一看,是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日历。他没说话,只是把日历递给我,翻开的那一页写着:“三月十七,潮退时见影。”
我抬头想问,他人已转身离去,步伐稳健却不急促,像完成了一项早已演练多次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