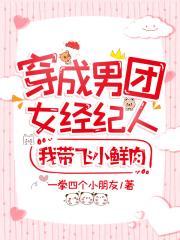笔趣阁>俗仙 > 321烟花三月楼发福利了(第1页)
321烟花三月楼发福利了(第1页)
陈乾六说道:“竹影愿意镇守此地甚好。”
他传授查竹影操控接仙宫的法诀,以及挪移阵法的用法,就带了两位师姐和其余门人回去了符离集仙市。
他还要上至高天,去勾兑官司,故而先把门徒都遣散,俞轻鸿。。。
风穿过山谷,带着沙粒与旧尘的气息,拂过那株墨心莲时,竟凝滞了一瞬。莲叶微颤,不是因风,而是像被某种无形之手轻轻托起。花瓣中央的蓝蕊忽然亮了一下,如同心跳,随即一道极细的光丝从花心射出,斜插入地,沿着青铜门前的石阶蜿蜒而下,如血脉回流。
这光不灼目,却穿透了百年的寂静。
远处山脊上,一个身影缓缓走来。他穿的是最普通的粗麻布衣,脚踩草履,背负一只竹篓,里面装着几卷泛黄的手抄本和一块磨损严重的盲文板。他的面容平凡得近乎模糊,左颊有一道浅疤,像是被火燎过,右耳缺了一角??那是幼年战乱中留下的印记。但他走路的姿态很稳,每一步落下,地面的沙砾都会微微震颤,仿佛大地在回应他的足音。
他是林小凡吗?没人能确定。
可当他走到青铜门前,蹲下身,将手掌贴在那株墨心莲的根部时,整座山谷的空气骤然变得稠密。
“你还记得我。”他说,声音低哑,却不容置疑,“我也记得你。”
话音未落,莲茎竟缓缓弯曲,叶片一张张翻转,露出背面早已刻好的文字??是《双轨识字法》第三章残篇,笔迹稚嫩,却是当年阿念初学写字时亲手所录。这些字原本应随她埋葬于西北戈壁,如今却在此重生,仿佛时间从未真正断裂。
青铜门内的虚空并未完全苏醒,但已有细微波动自门缝溢出。琉璃地面虽碎裂已久,其残片仍散落四周,此刻竟开始彼此吸引,缓缓拼合,如同受伤的骨骼正在愈合。浮岛虽已崩解,可那些由文字构筑的建筑碎片仍在空中漂浮,像星辰余烬,在夜色里闪烁不定。
那人站起身,打开竹篓,取出一本用油纸包裹的册子。封皮上无字,翻开第一页,只有两个凸起的盲文字符:“启”、“信”。
这是阿先生临终前亲手交给他的遗物,也是她一生整理的全部教学日志汇编。其中记录了三十七万两千六百一十九次授课过程,每一个孩子第一次写出“人”字的时间、语气、手势,甚至泪水滴落在沙盘上的位置,都被详尽记载。末页写着一行小字:
>“若有一天门再开,请替我去看看它是否还在等我们。”
他将册子轻轻放在门前石台上,又从怀中取出一支笔??不是毛笔,也不是电子触控笔,而是一截烧焦的树枝,来自当年焚书台遗址的灰烬堆。据说,那是最后一本《千字文》化为灰烬前,唯一未完全燃尽的部分。
他俯身,以枝代笔,在沙地上写下第一个字:
**“教。”**
笔画刚成,天地变色。
不是雷鸣电闪,也不是狂风暴雪,而是所有的声音突然消失。鸟鸣、风响、远处溪流……一切归于绝对静默。紧接着,这片沉默本身开始震动,频率越来越快,直至肉眼可见的波纹从“教”字向外扩散,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颗石子激起了整个宇宙的涟漪。
青铜门轰然洞开。
这一次,没有光柱升起,也没有虚影降临。门后不再是虚空星河,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由无数本书籍垒成的墙,层层叠叠,无穷无尽。每一本书都微微发烫,封面隐约浮现人名:有阿念,有阿先生,有那位东海老学者,还有更多陌生的名字,他们未曾留下画像,却留下了整整一生写下的教案、批注、日记、书信。
走廊尽头,悬着一面镜子。
他缓步走入,脚步踏在书页铺就的地面上,发出沙沙声响,宛如翻动旧课本。越往前行,两侧书墙越加炽热,有些书页竟自动翻动,浮现出动态影像:一个盲童第一次摸到“爱”字时笑了;一群聋哑少年用手语演绎《论语》时眼中含泪;火星基地的孩子们在红色荒原上用激光刻下“仁者爱人”四个大字……
终于来到镜前。
镜中映出的,不是他的脸。
而是千万张面孔的叠加??所有曾执笔授课的人,所有曾伸手写字的人,所有曾在黑暗中听见文字心跳的人。他们的表情各异,有的疲惫,有的欣喜,有的痛苦,有的坚定,但他们的眼睛都望着同一个方向:未来。
镜面忽然波动,如水面荡漾。一个声音响起,不是通过耳朵听见,而是直接在灵魂深处震荡:
>“你回来了。”
>
>“你不该回来。”
>
>“你必须回来。”
三种语调同时出现,却又浑然一体。
“我不是林小凡。”他低声说,“我只是个代笔人。”
>“林小凡从未存在。”镜中回应,“他是你们共同写出来的一个名字。就像‘老师’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选择。”
他闭上眼,再睁开时,眸中已有泪光。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拾起断掉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