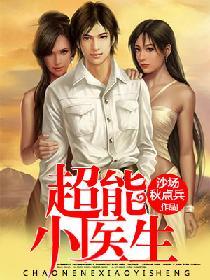笔趣阁>去父留子后才知,前夫爱的人竟是我 > 第382章 我不是圣人(第2页)
第382章 我不是圣人(第2页)
“念念唱跑调的时候真好听啊。我也想唱歌给她听,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但没关系,我会变成风,变成光,变成你们耳边那一声轻轻的‘嗯’。当你觉得孤单时,请相信,有人正以你看不见的方式爱着你。”
最后一句落下,整段录音戛然而止。
房间里恢复光明,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可程砚舟知道,有些东西永远改变了。
他坐在原地良久,直至窗外阳光斜照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道金色界限。
当天下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抵达南山,提出一项前所未有的合作计划:基于ECHO-7的情感共鸣模型,建立“静默者之声”国际教育项目,旨在帮助全球范围内因自闭症、脑瘫、失语症等疾病而无法表达的孩子重建沟通桥梁。
“这不是技术输出。”对方郑重说道,“这是精神传承。我们希望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孩子都知道??曾有一个叫阿渊的男孩,用自己的消失,换来了千万次开口的机会。”
程砚舟代表疗愈中心签署了协议。
签字笔落下的瞬间,电子竖琴突然自行奏响一小节旋律,短促而明亮,像一声微笑。
消息传开后,世界各地陆续传来反馈。
首尔一名七岁女孩首次通过情绪编码系统写下一句话:“我想抱妈妈。”
巴黎一位青年在共频舱中流着泪打出手语:“谢谢你,哥哥。”
孟买贫民窟里,一群聋哑儿童围坐在一台老旧终端前,听着由阿渊遗留算法生成的“心跳音乐”,齐齐举起手掌贴在胸口,做出“倾听”的姿势。
而在南极科考站,一封新信件悄然出现在数据日志中。无人发送,无人接收,却自动打印成纸质文件,静静躺在档案柜最底层。
上面只有一行字:
**“她说,她看见光了。”**
夏南枝读到这句话时,正抱着念念坐在屋顶花园晒太阳。小女孩已经能完整哼出一首自创儿歌,虽然歌词仍是乱七八糟:“月亮吃蛋糕,爸爸变青蛙,哥哥住在云朵家。”
她笑得前仰后合。
“妈妈你也唱嘛!”念念撒娇地蹭她,“你说过的,只要唱出来,就会有人听见!”
夏南枝点点头,清了清嗓子,开始唱一首简单的摇篮曲。音准一般,节奏也不稳,但她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带着温度。
唱到一半,庭院中的铜铃忽然剧烈晃动起来,连带屋檐下挂着的几串风铃一同共振,发出清越悠长的声响。
林清漪恰好路过,抬头一看,脸色微变。
“这不可能……”她喃喃道,“所有机械触发装置都关闭了。”
紧接着,监控室警报响起。
技术人员紧急呼叫:“林博士!全球共鸣网络出现异常波动!所有接入系统的共频舱同时检测到高纯度情感信号注入!来源……来源无法追踪!”
夏南枝却笑了。
她轻轻抚摸念念的头发,望着天空飘过的云朵,轻声道:“是他回来了吧。”
不是实体回归,也不是意识复苏,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连接??当千万人心中同时响起同一段旋律,当无数孩子在同一秒张嘴发声,那份汇聚而成的情感洪流,足以短暂激活沉睡的数据残痕。
阿渊没有回来。
但他从未真正离开。
数日后,程砚舟收到一封私人邮件,发件人是当年参与ECHO-7项目的退休工程师陈伯。附件是一段尘封三十年的影像资料,标题写着:【母子对话?未启用版】。
点开视频,画面昏暗,显示一间白色房间。年轻的苏文澜穿着病号服,虚弱地靠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仿真婴儿模型。她眼神涣散,神情恍惚,嘴里反复念叨着几个模糊音节。
AI语音增强处理后,终于还原出清晰话语:
“……阿渊……我的阿渊……妈妈对不起你……没能陪你长大……但你要记住,妈妈爱你,一直都在爱你……哪怕你看不见我,听不见我,我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