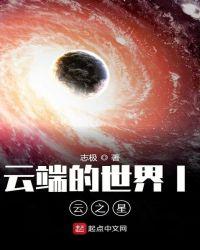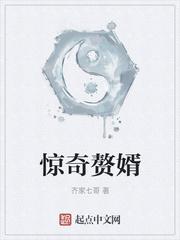笔趣阁>救命!我的心声它想害死我! > 字字都要命啊(第1页)
字字都要命啊(第1页)
沈见微本以为,所谓“协作”,就是在曹直那不容置喙的拟稿的节奏里做个安静的工具人,抄抄书、捡捡例子、递个茶水什么的,主打一个“听话”和“隐形”。
结果第二天才刚坐定,凳子还没焐热,就被派去整理后例附稿。
“你看赦令例稿,从近三年往前推,找赦罪用例四条,表明出处、目的、格式。字数控制在四百字一条。”曹直的声音毫无波澜,仿佛再说“去倒杯茶”。
【四条?四百字?字字都要命!】
这句话听起来轻飘飘地没什么杀伤力,落到沈见微手里却变成了厚厚一沓史书、公文、历年诏录,沉得她手腕发酸,案头瞬间被淹没。
【我是不是对“协作”这个词有什么误会,这分明是主将下令,小兵挖矿啊!】
沈见微盯着摊在案上、字迹密密麻麻的赦罪诏令,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开始她的“挖矿”工作。
曹直没有催她,只在上首伏案,一笔一划起草正文。
这种搭配乍看毫无互动,实则让她有点如履薄冰、压力山大。
【何止压力山大,简直就是泰山压顶!他在那写字跟刻碑似的,我这边喘气都不敢大声!】
因为她写的后附,不仅要找对例子,还得写得简明扼要、结构得当。最要命的是,它必须和曹直起草的主文严丝合缝——不能重复、不能冲突、还得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沈见微几次对照草稿和自己的例稿,从开篇主旨到赦令目的,再到赎罪条款的具体表述、原文如何精准引用……每一个细节都得小心翼翼。一句话不顺,一个用词不当,就有可能招来曹直那个“你是不是根本没读过书”的眼神凌迟。
她很快沮丧地意识到,自己找的例子虽然都“对”,可有些格式、顺序、措辞,并不完全契合曹直正文那严谨到苛刻的逻辑链条。
于是,沈见微犹豫再三,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指着自己稿子上的一处,“曹编修,我这个‘德音宣下’,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赦罪类诏书的起句?我看它在登基、赦狱的案例也用过不少次。”
【问出来了!问出来了!曹直不会觉得这问题蠢得冒烟吧?】
曹直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停下笔,抬眸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平静无波,却带着天然的审视感,语气平淡但不失挑剔,“‘德音宣下’可用,但你这段讲的是‘宥罪有度’,核心在论邢理、明法度。开头若用此泛泛之语,气势虽足,却易偏离主旨,反而削弱了‘宽宥’的针对性。”
他顿了顿,补充道,“你若想用它,放在收尾处承转过渡,引出宽仁之意,更妥。”
沈见微一愣,低头再看自己稿子上那句孤零零的“德音宣下”,顿时觉得它像个不合时宜、多余又碍眼的花边。
【完了,曹直肯定觉得我脑子不好,连这种问题都考虑不过来呜呜!】
她默默把那四个字用力划下,像在抹掉一个耻辱的印记,重新开始思考逻辑顺序。
【重来重来,这次一定要抠到每个字缝里面去!让曹直看看什么是“士别三时辰,应当刮目相看”!】
下午过半,沈见微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眼力和脑力,总算从故纸堆里淘出四条最符合赦罪目的的、格式严谨的诏令,整理出一份她自认为结构清晰、措辞准确的后附样本。
她像捧着易碎的珍宝,小心翼翼地递给曹直,“曹编修,我这边大概理了一个框,您看看可不可以?”
【千万别打回来重写啊!再抄一遍我的手真要断了!】
曹直接过来,目光快速扫过,速度极快,却让沈见微感觉像过了半辈子。他不置可否,只伸手指了指其中一条,“第二条用词太散。‘恤狱’与‘释囚’不能并列混用。”
沈见微心头一紧,急忙改口,“是。那我只写‘恤狱’?”
“你既写的是赦罪后附,”曹直的生意依旧平淡,“就别写‘恤’。‘恤’是行政层面的抚慰手段,非是法理上的直接赦免。此处需用更明确的赦免用语。”
【……果然!每个字都有讲究,每个词都有坑!这差事真不是人干的!‘恤’也不行?这词招谁惹谁了!行吧行吧,您是祖宗,您说了算!】
她不敢再多嘴,只埋头认命修改,力求精准。
曹直倒也没再多说什么,审完稿子就回头继续他自己的正文,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拨正了一粒尘埃。
这反而让沈见微心里生出了一点莫名的感激。
【还好……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嘲讽我,也没有让我重写十遍。谢天谢地曹编修手下留情!】
因为他批评得很冷静,不含个人情绪,甚至有点……像是认真对待她这份虽然稚嫩但也尽力了的劳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