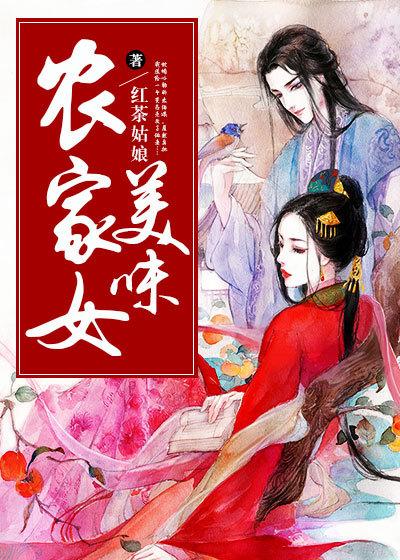笔趣阁>权宦对朕图谋不轨 > 皇后的慈心(第2页)
皇后的慈心(第2页)
“邵厂督言下之意是?”她看着邵钰那副从容的模样,微微眯了眯眼。
“治病不信药石而靠通灵之法,实在荒谬,此法也是难以在天下立住脚跟。”
“至于如何离开这翊坤宫,还得仰仗殿下了。”
闻言思量片刻,她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有力,“好生礼待那术槐,别叫人挑出了错,他要求的那些物什,一律不准调换,我们大胆用。”
“明日找几个人在城中宣扬皇后此法,务必要传到江南发时疫的地方,让大家一同看看皇后娘娘是母仪天下还是蛇蝎心肠。”
她望向窗外被高墙框住的四方天空,目光有些茫然,皇后此招是救命的良方还是害人的邪术,全都由她云灼说了算,天下人如何看她,也由她说了算。
殿内安神香的气息淡淡弥漫,却丝毫无法安抚其中涌动的暗流与杀机。
棋局已布成,不能光紧着黑子运筹帷幄,也该轮到白子反击了。
翌日
金喜将早膳布好后,四下确认无人后,将袖中的信递给云灼。
“殿下,这是御使大人的回信。”
云灼扫了一眼,见信中字里行间全是关心之意,闭口不提朝堂之事,心下便已明了江墨生所想,如此看来,将江家收入麾下不是易事。
她面上不露声色,默默将那信丢进火盆子里,直勾勾盯着那火舌吞噬信纸。
“殿下,大人怎么说?”
“揣着明白装糊涂,跟我打太极呢,姑姑,江家不信任我,也不想淌这趟浑水,此事或许要费些功夫。”
“奴婢日后多多去江府劝劝大人就是,大人一向是个嘴硬心软的人,不会放任您不管的。”金喜拍了拍她的肩头安慰道。
“他或许可以作为长辈对小辈那样对我心软,但绝不可能堵上江家的未来,在朝公事上对我心软。”
云灼咬了一口精致的点心,慢悠悠咽下后才道,“不可,邵钰那边未尝没有找人盯着翊坤宫,你总出去会惹他怀疑。此事急不得,我再想办法就是。”
“您为何不直接拿出家印,这样他也心服口服。”
“姑姑,你想简单了。若我没猜错,那支兵应当是江墨生在管着的,我即使有家印,但天高皇帝远,我无法出面,江墨生不服我,那支力量便不能真的为我所用。”
“况且,我病秧子的名号在外,江墨生若是个聪明人,便不可能冒风险与皇后做对,把宝押在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太子身上,更何况,他一向厌恶阉党,邵钰强势,江墨生也更不可能与我坦诚。”
金喜张了张口欲要说什么,云灼余光便瞥见邵钰那玄色锦袍,于是给她使了个眼神,二人这才算完。
“殿下怎么不说了?有什么事是奴婢不能听的?”邵钰见金喜神色僵硬,眼尾微微挑起,轻笑一声道。
“姑娘家的私房话罢了,邵厂督也想听吗?”云灼放下手中的汤羹,从容抬眼对上他墨黑的眸子。
“那倒不必。”
“邵厂督这会儿子来,可有什么事?”
“还未有一个时辰,京城便已传开了皇后心慈,你在他们眼里,如今也是个活了今日指望不上明日的主了。”
云灼轻轻点了点头,“你且看着就是,好戏才刚开场,不急。”
她觉得今天的羹格外香,自己伸手又盛了一碗,抬眼便看到邵钰正盯着她看,眼底闪过一丝玩味。
云灼进了一小口羹,被他盯得实在不自在,忍不住抬头,“邵厂督要与本宫一同用膳吗?”
话音还未落地,邵钰便不客气地坐在了她对面,自顾自给自己盛了一碗,“盛情难却,多谢殿下赏这顿,奴婢四更天便醒来办事了,到现在还滴水未进。”
云灼不想听他贫嘴,忍了他的放肆,将面前的盘子往他那边推了推,“多吃点,吃饱了好给本宫用心办事。”
“那是自然,就冲今日这碗羹,奴婢便把一切都奉献给陛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不正经的死太监。
“你昨日信誓旦旦与本宫说,离开翊坤宫易如反掌,你的办法想得怎么样了?”
邵钰闻言,眼神飘向她的脸,似笑非笑,“不知陛下可愿舍身?”
闻言,她愣了一下,随后又像是反应过什么来一般,面颊浮上一抹红晕,轻咳了一下,忙又板起了脸,“不是说吃了那碗羹便可为本宫赴汤蹈火吗?这般放肆,小心本宫治你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