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高嫁公府 > 第45章(第2页)
第45章(第2页)
贺知砚哪见过她这种不要命的模样,一时唬的愣住,一边捂脸绕着桌子跑着,一边骂道:“江氏,你真是疯了!”
江氏两眼含泪,手里的鸡毛掸子挥得虎虎生风,哭着喊道:“你要是敢把嘉月赶回沈家,我今天就不活了,我与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同归于尽!”
贺世子往前躲着,不小心被椅子绊了一下脚,那鸡毛掸子就顺势破风而来,直往他脊背上狠命地砸。
他手忙脚乱地得从地上爬起来,道:“江氏你个疯子,住手!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了就是!”
江夫人哭骂道:“你个没良心的,你知不知道女儿在沈家受了多少苦头?当初你将那沈家畜生夸得天花乱坠,你是不是收了沈家孝敬你的银子,把女儿往火坑里推?”
一听她到提到这个,贺世子便有几分心虚,当初沈绍祖是孝敬了他不少银子,他只当沈家家资丰厚,哪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江夫人又哭又骂,他便没底气与她还嘴对骂了,提着袍摆捂着红肿的脸急急忙忙往外跑去。
跑出院门前担心江夫人再追过来,回头时果然看见她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慌得下台阶时踉跄一步摔了个狗啃泥。
贺世子暗骂一声倒霉,忙不迭慌慌张张爬了起来,狼狈地捂着脑袋,一瘸一拐地飞跑着往外走,对院里的丫鬟喝道:“一个个都眼瞎了不成,还不拦住她?”
月华院的几个丫鬟原本还担心江夫人被世子爷打了,现在见夫人没吃半点亏,都装作没看见没听见,没一个上前拦着。
贺世子骂骂咧咧跑远了,江夫人也没追出院去,她身体本就病弱,这下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由夏荷搀着回了正房,喘了半天的气,激动的心跳才平缓下来。
不过脸上的泪还没干,眼里依旧含着一汪泪哭着。
姜忆安来月华院的时候,江夫人靠在榻上躺着,脸上都是愁色。
看到长媳来了,她疲惫地笑了笑,道:“忆安,你坐下,我有话对你说。”
姜忆安在她榻旁坐了,端起小几上的汤药轻轻吹凉,道:“母亲有什么事?”
江夫人默叹了口气。
女儿和离的事,她是不敢指望贺知砚那个丧良心的了,他能不横插一脚阻拦就不错了。
与丈夫厮打了一顿的事,江夫人也不好意思说,想了想,她只道:“再过几日,嘉月就出小月子了。我寻思着,那沈家你妹妹是不能再回去了,我想让嘉月与沈家和离,这原也是你妹妹的意思,你觉得呢?”
婆母竟然如此干脆利落地想让贺嘉月和离,姜忆安有些意外。
她微微挑起眉头看着江夫人,不动声色打量了她几眼,似在确认婆母是一时冲动,还是深思熟虑过了。
江夫人看见她眸中的惊讶一闪而过,不由坐直了身子道:“你这个丫头,别以为我也总是个软脾气的,当娘的怎会让自己孩儿受苦,这次我是下定决心的了。”
姜忆安灿然一笑,扶着她的胳膊让她躺下,她看得出,婆母方才像是动了大气,这会子情绪还有些激动,眼睛也红红的。
“娘跟我说这个,我自然也是支持的,妹妹想要和离,我只会为她高兴。”
听见这话,江夫人放了心,眼里却又含了泪。
国公爷担着九省提督的重任在边境巡视,不知何时才能回府。
她虽是十分害怕公爹,可若是公爹在府里,她去求上一求,女儿和离的事便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现如今公爹不在府里,她身体又病弱,女儿和离的事,还得指望长子长媳。
江夫人握着长媳的手,沉声道:“忆安,你妹妹与沈家和离的事,还得你和晋远操心。”
姜忆安笑了笑,道:“娘放心吧,不是多大的事,只要嘉月坚决想要与沈家和离,就不会有问题。您别担心,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养病。”
~~~
晚间沐浴过,姜忆安换了一身柔软舒适的石榴色寝衣,走到桌案前,将烛火拨得更亮些。
不一会儿,贺晋远亦沐浴过,穿着白色的寝衣,黑色缎带覆着双眸,手中拿了一本书册,慢慢走了过来。
姜忆安一手拿起烛台,走到他面前举着烛台晃了几晃,没话找话地道:“夫君沐浴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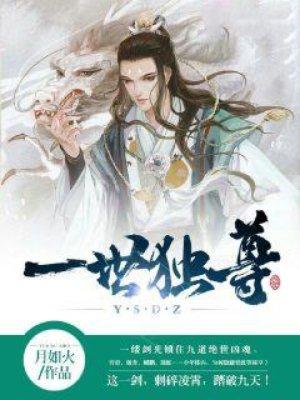
![拯救偏执反派boss[快穿]](/img/2878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