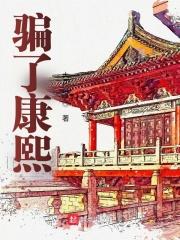笔趣阁>碎玻璃 > 没有家(第1页)
没有家(第1页)
夜晚,在市内的唯一一所高档酒店里,夏迩闭目躺在床上。他没有生病,只是睡着了不愿意醒,紧闭的双眸除了无意识地渗出眼泪,无论怎么呼唤他,都不会有些微颤动。
就连张绮年帮他脱下厚重的毛衣,那噼里啪啦的静电炸得他手疼时,他都没有反应。
张绮年宽厚的手掌轻抚着夏迩的脊背,在这芦苇一般细瘦的身躯里,他的成就感得到了满足,尽管卑劣,但仍旧是成功。
让这孩子躺在自己怀里,借灯光欣赏他泫然的漂亮面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占有是如此的简单,从来都只是时间问题——张绮年如此思忖着,只需找准契机,伸出臂膀把他揽在怀里,他动弹不得,就像只淋了暴雨的兔子,在山洞里瑟瑟发抖,畏惧着黑暗,却也无法离开这洞穴的保护。
张绮年在睡着的夏迩唇上轻轻吻了吻。
在这个时候,在他将夏迩脱了个精光为他换上柔软的睡衣的时候,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到下一步的,他渴望建造美丽的建筑,也渴望见到美丽的事物臣服于自己的身下。大概人活着就是为了征服世界,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罢了,张绮年很清楚自己,于是当夏迩睡着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做。
如果是以这种方式的话,在很久很久之前他就该得到了。
他想看夏迩像只小兔子般蹦蹦跳跳地扑进自己的怀里,欢欣地笑着,往他怀里钻,在他的身体中汲取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张绮年从泥淖里走出来了很多年,却依照惯性不断地继续力量,此际的体内存续了太多的生命力,他渴望去拯救某个人,渴望某个人能够死死地抓住他,赐予他一个救世主的身份。
如果非要对他这份感情刨根问底的话,这便是最真实的答案。
晚上,他和夏迩共枕而眠,他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第一次感受到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过去在酒局上他也抱过他,却从未像这一刻这般静谧。他不再挣扎了,在自己怀里,睡得像个孩子,不,他本来就还是个孩子。
十八岁,张绮年都记不得自己十八岁时是什么模样了。
他只记得,粘在身上的水泥味似乎怎么都洗不掉,连带他的自尊,都带上了灰尘和贫穷的味道。
兀自放飞神思,张绮年阖上眼睛,开始思考起怎么帮夏迩解决这个难题。
他家的问题说复杂也不复杂,无非就是钱的问题,但绝不简单,因为夏迩这个爹不是个省心的主。在警局里打电话,第一个打得不是家里人而是张绮年,他也做得出来。分明知道自己对他儿子的意思,还三番两次来要钱,跟卖儿子有什么区别。
可没了这个爹,夏迩还会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自己身边吗?
张绮年绝非正人君子,他向来以结果和利益为导向。如果夏父有用,尽管是个麻烦,但到底是个有用的麻烦,他对此甘之如饴。
驱赶思绪,张绮年把夏迩往怀里搂了搂,他罕见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张绮年就站在窗边打电话,这时送早餐的服务员推着餐车摁响了门铃,张绮年开门后,对他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服务员看到了床上还在沉睡的夏迩,立即收回了目光。
摆好餐具,斟上咖啡,服务员知趣地离开。
张绮年挂了电话,坐到了床边。一夜过去,夏迩那睫毛依旧是濡湿的,眼泪时不时渗出,仿佛没有止境。
他轻轻摇了摇夏迩。
“迩迩,起来吃点东西。”
夏迩不动,但张绮年看得出来,他醒了,只是不想睁开眼睛。
张绮年温柔地笑,说:“没什么事是不能过去的,先起来吃点东西,之后要睡多久睡多久。”
夏迩依旧不动。
张绮年意味深长地看他,沉默了一会,继续说:“你是害怕面对现实,还是害怕睁开眼睛看到我?”
他凑近了,侧卧在夏迩身边,半撑起身子,自上而下地凝视他,用手背轻轻抚着夏迩的脸庞,“迩迩,知道什么是现实吗?现实就是你想和不想,它已经是那个样子了,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你的逃避而有任何改变。你要做的只能面对,接受。现在你的现实就是,你的母亲在上海的医院里接受治疗,你妹妹得到了妥善的照顾,有律师在为你那个老爹来回奔走,你现在在我身边。”
张绮年在夏迩胸口一点,“你在我身边,明白吗?”
夏迩的睫毛颤动,最终缓缓睁开。
张绮年映在他那双如水般的浅色眸子里,是微笑着的。夏迩看了他一眼,艰难地撑起身体。
张绮年扶起了他。
“对,这才听话。”张绮年钳着夏迩的胳膊,把他摁在了餐桌旁,俯身在他身边轻声说:“吃完早餐,跟我回上海,酒吧那边我已经给你辞职了,我的人,是不能在那种地方工作的。”
他抚摸着夏迩松软的、带着热气的卷发,在他面颊上吻了吻,“音乐学院的老师在等你,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学生的,是吗?”
自始至终,夏迩都一言不发,他沉默地吃着早餐,苦涩的眼泪随面包一齐咽下。张绮年坐在他对面,满意地看着他的小男朋友一口一口地细嚼慢咽着。他知道此时夏迩的顺从有几分报复的意味,但他始终相信时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