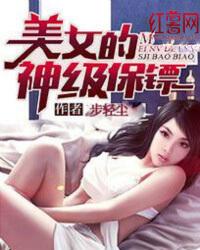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二百八十一章 小三元(第1页)
第二百八十一章 小三元(第1页)
“吓!春哥儿又是第三?!”大伯娘紧紧抓住小婶的双手,幸福得快要晕过去,“咱们春哥儿也是秀才了?哈哈哈!我终于可以当婆婆了!”
“是啊,咱家祖坟冒青烟了!”小婶奋力挣脱不得,只好放弃了挣扎道:“以。。。
夜色如墨,寒风穿堂。苏录坐在书案前,烛火摇曳,映得他眉目沉静。窗外北风呼啸,吹得檐角铁马叮当乱响,屋内却只闻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他右手执笔,左手轻按稿纸一角,额角沁出细汗,却不曾抬手擦拭。
这一篇策论,已写了近两个时辰。
题目是“御边三策”,出自今科会试真题。虽非当场亲历,但苏录为求实感,仍照规制闭门三日,焚香沐浴,辰时开卷,酉时停笔,中途不饮茶、不交谈、不离座。连老仆送饭来,他也只摆手拒之。他知道,这不仅是一次模拟,更是对心志的磨砺。
殿试在即,天子亲策,万众瞩目。而他从一介布衣走到今日,历经乡试、会试两场鏖战,早已明白:八股取士,看似拘于格式,实则包罗万象;策论一道,尤重见识与胆略。若无真才实学,纵使辞藻华丽,也难入主考法眼。
此刻他所写的,并非应试之作,而是心中久蓄之言。
“臣闻御边之道,不在城高池深,不在兵多将广,而在民心之向背、国势之盈虚……昔汉武拓西域,唐宗抚突厥,皆以威德并施,恩信兼行。然近代以来,边患频仍,岁币年增,非敌之强,实我之弱也。弱者何?政不出中书,令不行于外镇,财竭于内耗,兵疲于冗食……”
写到这里,他顿了顿,目光微凝。
这些话,太锋利了。
若是考官开明,或可视为忧国之语;倘若遇上守旧之辈,怕是要落个“讥讽朝政”的罪名。但他终究没有删去,只是轻轻吁出一口气,继续写道:
“故欲固边防,先清内弊。裁冗官以省费,核屯田以养兵,修驿路以便运,练乡勇以辅戍。此四者立,则国用足;国用足,则军威振;军威振,则虏不敢南下而牧马……且夫天下之大患,不在塞外风雪,而在庙堂晏安。君若勤政如贞观,臣皆尽责似房杜,何愁胡马嘶鸣于郊畿哉?”
最后一句落下,他搁下笔,缓缓闭目。
良久,睁开眼时,眼中已有血丝,神情却愈发清明。
这篇策论,他没打算藏拙。他知道,殿试之上,拼的不是谁更稳妥,而是谁更有担当。皇帝要的不是一个只会背诵经典的书呆子,而是一个能直面时弊、提出对策的治世之才。
窗外月光斜照进来,洒在案头那本翻得卷边的《资治通鉴》上。那是他自少年起便随身携带的书,页页批注,密密麻麻,如同他一路走来的足迹。
次日清晨,苏录将此文誊抄一遍,封入信函,遣人送往恩师李阁老府上,请其斧正。
李阁老乃当朝礼部尚书,三朝元老,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三年前在京师初见苏录,便惊叹其才:“此子胸有丘壑,非池中物也。”此后屡加提携,视若己出。
午后,仆人带回回信,仅八字:“锋芒毕露,然不负望。”
苏录读罢,嘴角微扬。
他知道,这是鼓励,也是提醒。
当晚,他召集家中几位同窗好友,在书房设宴小酌。几杯酒下肚,气氛渐暖。有人问起殿试准备如何,苏录笑道:“不过尽人事耳。”
座中一人摇头道:“你何必谦逊?今科状元,舍你其谁?”
另一人附和:“正是。前番会试文章传遍京华,连内阁几位大学士都赞不绝口。听说张相公还特意命人抄录存档,说‘五十年未见如此雄文’。”
苏录举杯轻啜,神色淡然:“诸位莫要捧杀。科场之事,变数太多。才学只占七分,其余三分,系于运气、体魄、乃至考官心境。况且,天下英才何其多?江浙有沈明远,湖广有陈子昭,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文采斐然?我岂敢称首?”
话虽如此,众人却知他胸有成竹。
席间谈笑正酣,忽听门外脚步急促,一名小厮推门而入,脸色发白:“少爷!不好了!刘府派人来说,刘小姐昨夜突发急症,已经昏迷一日一夜,郎中束手无策!”
满室喧哗戛然而止。
苏录手中的酒杯“啪”地落地,碎成数片。
刘小姐,即是刘婉儿??他的未婚妻,也是他此生唯一动心动情之人。
三年前,他在扬州乡试放榜之夜偶遇婉儿。彼时她正替父誊抄县志,一袭素裙,眉目如画,执笔的手纤细稳定。两人因一部《孟子章句》争论半宿,竟至忘眠。后来得知她是知县独女,家教甚严,婚事由父母做主。可她父亲一眼看中苏录气度不凡,主动提亲,约定待其登第后完婚。
三年来,他们通信不断,情意日笃。每逢节令,必互赠诗词。去年中秋,婉儿寄来一幅亲手绣的荷包,上面绣着两句诗:“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苏录泪湿衣襟,连夜回诗一首:“此心如明月,夜夜照君台。”
如今她病危,怎叫他不惊?
他猛地站起身,连外袍都来不及披,便往外冲去。
“苏兄!”有人喊住他,“你现在去也无济于事,不如先请太医!”
苏录回头,双目赤红:“她等不起!我在京师举目无亲,唯有我能护她周全!”
说罢,冒雪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