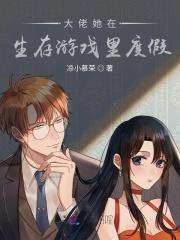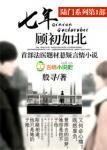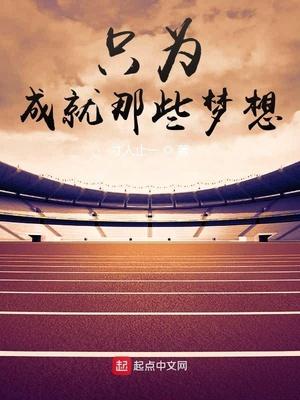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1977大时代方言朱琳无广告免费大结局 > 第1405章 老胡的防备心刘曼玉一天送两次礼(第2页)
第1405章 老胡的防备心刘曼玉一天送两次礼(第2页)
正是因为想给人留生路,才不得不给动物让路。
你以为我们在架电线?其实是在重新学会走路??轻一点,慢一点,别踩疼了大地。”
两人沉默地喝着汤,窗外风声掠过林梢,如同电流穿过绝缘层。
远处一道微弱红光闪烁,是边境监测站的警示灯。
阿依古丽忽然问:“你说,如果有一天,整个地球都被‘大地脉搏’覆盖,每一盏灯都能感知周围的生命,会不会……太吵?”
“不会。”
巴彦摇头,“真正的智能不是无处不在的亮,而是知道何时该熄。
就像呼吸,有进有出,才有节奏。
我们的电网也该有心跳,有梦境,有静默的时刻。”
她点头,望向墙上挂着的老式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村级电站的位置,红线如神经网络般交织。
其中一处被红笔圈了又圈??那是西藏双湖县的一个游牧点,海拔五千一百米,全年大风天超过两百日,曾三次尝试通电失败。
“下周我要去双湖。”
她说,“他们用柴油发电机撑了八年,去年冬天冻坏了两台,孩子写作业只能靠煤油灯。
启明学院新研的抗低温储能箱已经测试完毕,我想亲自去看看安装效果。”
巴彦皱眉:“那边现在已经开始飘雪了。
你确定要这个时候去?”
“越冷的地方,越需要光。”
她笑了笑,“而且,我不只是去看安装,还想听听牧民怎么说。
技术能送到门口,但能不能走进心里,还得看他们愿不愿意开门。”
翌日清晨,她搭乘直升机飞往羌塘。
航线穿越唐古拉山脉,机身剧烈颠簸,舷窗外云层厚重如铅。
飞行员通过耳机提醒:“前方有强气流,建议绕行。”
但她坚持原定路线:“下面有个小学,今天举行通电仪式,我不想迟到。”
当飞机终于降落在临时平整的草甸上时,风速已达八级。
一群穿着厚棉袄的孩子列队站在校舍前,手里举着褪色的国旗和手写的欢迎牌。
校长迎上来,声音几乎被风吹散:“阿依老师!
我们等了二十年!
昨天还有家长骑马三十里送来酥油,说‘灯亮了,得供菩萨一样的礼’!”
她走进教室,四壁斑驳,黑板裂了缝,但每张课桌上都摆着一台崭新的LED阅读灯。
技术人员正在调试储能箱,外壳印着藏汉双语标识:“光明驿站?高原特供”
。
启动按钮按下那一刻,灯光齐亮,孩子们齐声惊呼,有几个甚至跪下来合十。
一位老阿妈颤巍巍上前,捧出一条洁白的哈达,嘴里念着经文。
翻译小声告诉她:“她说,你是雪山送来的光之使者,愿佛祖保佑你的眼睛永远明亮。”
阿依古丽跪下,额头轻触老人的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