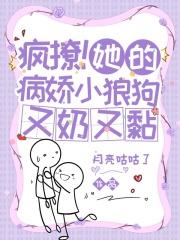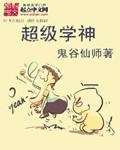笔趣阁>祥子修仙记 > 第197章 拦住李家一人都不能放走6K(第2页)
第197章 拦住李家一人都不能放走6K(第2页)
“你看不见声音,但你能感觉到它。”他对她说,“就像风吹过皮肤,像心跳震动胸膛。只要你还在感受,你就没有真正沉默。”
小女孩用力点头,眼中闪着光。
某日黄昏,徐彬终于醒来。他躺在草屋里,望着屋顶茅草间的星空,久久不语。祥子端来一碗药汤,放在床头。
“你睡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他说。
徐彬缓缓转头看他,声音沙哑:“我……做了很长的梦。”
“梦见什么?”
“梦见我把火把扔进村子的时候,听见了母亲的歌声。她不是在骂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唱……那首我小时候最爱听的童谣。”
祥子沉默片刻,轻轻坐下:“她从未恨你。她只是希望你能回来。”
徐彬流泪:“我还能回去吗?”
“你现在就在家。”祥子说,“而且,你还有事要做。”
“什么事?”
“重建清音司。”
徐彬愕然。
“不是那个被权力扭曲的机构,而是真正的‘清音’??清理虚假之声,传递真实之音的地方。”祥子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需要有人整理那些因钟声而复苏的记忆,需要有人记录每一份忏悔与救赎,更需要有人告诉世人:声音不该被垄断,言语不应被审判。”
徐彬久久凝视着他,终于缓缓坐起,握住了他的手。
半年后,一座新院落立于西漠边缘,无墙无门,仅有数十口大小不一的铜钟悬挂檐下,随风自鸣。院门前立碑,上书三字:“清音坊”。
这里不分贵贱,不论身份,任何人皆可前来诉说心事。有老兵讲述战场上的谎言,有女子控诉夫家多年的虐待,有官员坦白受贿真相,甚至有前噤声使跪地忏悔过往罪行。每当有人说完,便会有人轻轻敲响一口钟,表示“此声已被听见”。
消息传开,四方来者络绎不绝。有人说这是疯癫之举,迟早酿成大乱;也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太平之基??唯有当痛苦得以表达,仇恨才不会沉淀为暴戾。
又过两年,北疆战事再起,敌军压境,百姓流离。朝廷欲征壮丁十万,强推“镇国钟律”,以统一号令。消息传出当日,清音坊内钟声齐鸣,持续九日不绝。第九日清晨,全国各地突然同时响起相同的旋律??正是《归音引》。
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不持兵器,不呼口号,只是静静地站着,听着,然后一同哼唱起来。
军队停下了脚步。
皇帝在宫中听见窗外传来的歌声,颤抖着掀开帘幕,看见整座皇城的人都站在街上,仰望着天空,轻声吟唱。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了幼年时母后教他的第一支歌。
三天后,圣旨下达:废除禁钟令,赦免鸣社成员,召祥子入京问策。
使者来到清音坊时,却发现人去屋空。只留下一封信,置于最大的那口钟下。信上写道:
>“吾志不在庙堂,而在人间。
>若陛下真心求治,请允百姓开口,许万民发声。
>钟声自有分寸,人心岂容封锁?
>一日有声,一日不亡。”
使者带回信件,皇帝读罢良久,命人将信裱于御书房正壁,并亲笔批注八字:“声为民本,缄者自盲。”
自此,天下风气渐变。言论虽仍有管控,但已不再以“静默”为最高准则。各地兴起“鸣堂”“音馆”,专供平民陈情议事;科举新增“听音策论”,考察学子对舆情民意的理解;甚至连刑狱审案,也开始重视被告的陈述与情感表达。
十年之后,祥子的名字已成为传说。有人说他云游海外,寻访远古音灵;有人说他化作风中一缕回响,永驻人间;还有人说,每逢月圆之夜,若静心聆听,仍能听到一口无主铜钟独自轻鸣,像是在呼唤,又像是在安慰。
而在那北方荒原的石碑前,野花依旧年年盛开。某一日清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拄杖而来,放下一束紫菀,低声说道:
“娘,我回来了。”
她是秋纫。
身后,一个小男孩好奇地问:“奶奶,这块碑上写的是什么意思?”
秋纫抚摸着碑文,轻声念道:
“伪声可封,真音不灭。
裂心之处,即是归途。”
“意思是啊……”她抬头望向远方,“就算世界想让你闭嘴,只要你还记得疼,就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