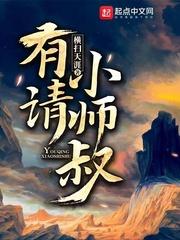笔趣阁>汴京食滋味 > 3035(第5页)
3035(第5页)
然而胡六嘀咕了好几句,显然搞不明白,为何青蛙的一双眼睛会凸起在头顶上像熊的耳朵那样,这超出了宋朝人的理解范围,但他还依照客人的意思做了。
做出来的土窑晾干后就是个遁地的青蛙头,在院中也算一道亮丽的风景。
江暖把陶盆倒扣过来,用筷子敲得梆梆响,美其名曰:“这是敲锣打鼓,也是喜庆。”
被凌花追得满院子跑:“你也和晓哥儿似的学皮了是吧,那陶盆不能敲,会裂。”
江晓叭地吐了一口口水泡泡,以为娘亲要祸及他呢,咧嘴一笑,也随江暖一起,一圈圈跑得起劲。
打不着人的凌花气喘吁吁,刚一停脚,后头唰地冲上来一只黄白小狗,四条小短腿跑得飞起。她忍俊不禁:“小东西,还真有点看家护院威风凛凛的样了啊。”
就这样,人在前头跑,狗在后头追。至于容双,早笑成了软软一滩,抱着肚子靠在椅子上,险些直不起身了。
在人与狗的笑闹声中,江知味用秸秆引燃两根木柴,统统塞进土窑中。
土窑和后世的烤箱一样,都得先预热。趁这个时间,便能剁肉馅儿、擀皮子做锅盔了。
今日预备做三个口味的锅盔。其中梅干菜肉馅儿是专给孩子和狗子准备的,入口咸香,不油不辣。
另外的甜辣口是给容双这个嗜辣狂魔特制的。放多多的茱萸和白糖,甜与辣交织相叠,吃起来相当过瘾。还有白糖馅儿的锅盔,面皮子微甜、薄脆,嚼起来跟薯片似的咔嚓咔嚓响,特别香。
面团已经备好。用老面做的面引子,温水化开兑到面粉里,加一块猪油,揉到“三光”——面光、手光、盆光,静置醒发。醒好的面团切成小剂子,搓圆,刷上猪油,再次醒发,这是面饼酥脆的关键。
肥肉掺半的肉馅中,加入洗好泡发的梅干菜、十三香、盐、糖和少量黄酒,再滴几滴芝麻香油增香,加酱油、豆瓣酱,抓拌均匀。包在醒好压扁的面团中,用手拍扁,擀薄成牛舌状,随手撒一把飘香的芝麻粒儿,此为梅干菜锅盔。
江知味做梅干菜锅盔不喜欢放葱花。梅干菜本身的味道独特,下葱花反倒掩盖了原始的干香味,总让人觉得喧宾夺主。
至于白糖锅盔,做法就更简单了。同样的面剂子,包裹上白糖馅儿,留心擀的时候别把面皮擀破了,这样吃起来,外壳酥脆,里头还流糖心,甘甜得像是化了蜜水。
两头兼顾,柴火在窑中烧得滚热,一刻钟过,熄了火,用木板挡上闷一小会儿,到能进窑时,饼子恰好做好。
预热过的土窑滚烫。江知味用蘸水的布条包着手,将锅盔铺在铁篦子上送进去。
铁篦子是管李二狗家借的。江知味此前发现,他们家的小院子里时不时地冒起灰烟,烟之中,还总是夹杂着一股浓浓的肉香。
后来才知道,原是他们家的羊仔和虎妞都很喜欢吃爊肉,李二狗就专程在家整了个烧烤炉,隔三岔五烤肉给他们吃。
要说李二狗这单亲爸爸做得也不容易。妻子两年前因病去世,他白日里要照看孩子,到夜里,趁孩子睡着,就做闲汉替周边酒楼食肆的客人们跑腿买东西。
一年到头攒不着几个钱,全紧着给家里俩孩子买肉吃,却给自个儿养得精瘦精瘦的。
在他的看顾下,羊仔和虎妞茁壮成长,性子都落落大方。
虎妞四岁,奶肥奶肥的。羊仔则看着抽条了些,年七岁,长着比横桥子东巷里这些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们都要高壮,算是他们中顶天立地的存在了。
有一回江晓在巷子口玩摔了一跤,磕破了波棱盖,就是羊仔这个做哥哥的给背回来的。光辉伟岸的形象一树立,这位七岁的少年,顿时成了横桥子东巷的孩子王。
但偶尔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
比如上回巷子里的孩子们因为洗冷水澡着凉,追根究底,就是羊仔这个大哥带的头。这事被李二狗知道,他们家的爊肉味没了,反而有不少人听见院子里传来杀猪般的哭嚎。
江知味心想着,一会儿还铁篦子时,可得把锅盔给他家多送两个去。要没李二狗的慷慨相借,今日这锅盔,恐怕还吃不成呢。
渐渐的,锅盔的香味从土窑中散出来。
容双搬了张椅子,坐在土窑前守着。两小只也蹲在她身侧,时不时地仰脖,抬着鼻子小狗似的嗅嗅闻闻。
真正的小狗则乖巧地趴在太阳底下睡觉。起初还蜷缩着,后来愈发放松下来,翻了个身,露出肚子底下没长毛的粉色斑点小肚。任凭四下里人行来去,她都不挪窝、不动弹。
被木板盖着的窑洞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那是猪肉里油脂沸腾绽开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声油爆的细响,梅干菜和猪肉的香味愈来愈盛,飘飘然笼罩着整座江家小院。又兜兜转转离了墙头,向着横桥子东巷里的各家各户飞去。
“阿——秋——”
正挑水洗衣裳的李二狗,被香得打了个尖锐且绵长的喷嚏。想起一早知姐儿同他借去的铁篦子,不用猜都知道,这是又在捣鼓新的吃食了。
五脏庙不争气地扭曲在一起,李二狗瞬时饿得心慌。看看自家冰冷的灶房,没甚烟火气的小院子,还有俩噔噔噔跑出来、缠在他身侧一个劲儿嚷嚷饿的孩子。
今日本想躲躲懒,煮个稀粥凑合,可这满院子飘的一阵阵烤饼香,让他哪还有心思,去煮什么粥啊水啊。
“爹,太香了。我想吃肉。”虎妞都快哭了,眉梢透红,小嘴巴扁成了鸭子。
羊仔也闹:“爹,这就是江家二姐姐说的锅盔吗。爹,我饿了。爹,你咋不会做锅盔。爹……”
李二狗头皮发炸。吵是其次,关键是馋呐。不止孩子馋,他也馋得直咽唾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