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综漫同人)病弱六眼和她的软饭小白脸/天与暴君为爱白给 > 第133章(第3页)
第133章(第3页)
他捂着胸口,撕心裂肺地咳嗽。
“彭格列的人?”
咳得半死不活的少年听见他问。
“咳咳咳、什、什么……”
眼里开始盈满生理泪水,入江正一透过水雾看见男人把那盒关东煮放在椅子上,又走过去捡起深紫色的火箭筒。
“谁让你来的?”
禅院甚尔拎着火箭筒。
黑影慢慢落下,男人蹲下身,平视他。
那双手按在少年天灵盖上,轻飘飘拍了几下,打得他摇晃着。
入江正一好似二十级台风袭来时一枝独秀的树。
眼睛少年也不敢咳了,他死命咽下喉咙里声带的震动,汗如雨下,身体动也不动,噤若寒蝉。
“不说吗?”
禅院甚尔屈起的大腿肌肉有他肩膀那么粗。
入江正一使劲点头,脑袋点出残影。
他磕磕巴巴把这一整件事全程摊开了说给禅院甚尔听。
说完后,少年又把那张被揉皱的纸条转交给他。
他接过纸条,表情看不出信没信。
但男人的怒火似乎减弱了一些,看入江正一的眼神仍旧浸满杀意。
入江正一打着抖,忍着麻痹感从地上爬起来时,禅院甚尔正接着电话。
卫裤宽松,屈膝或者坐下时会绷紧肌肉,少年倒抽一口冷气,他认出了左侧口袋里的方形痕迹。
结合那张掉在地上的化验单、男人见到他后说的那句话。
不会吧……
入江正一两眼一黑,想一巴掌打死几分钟前的自己。
天呐!你都做了些什么啊入江正一!!
眼镜少年尖锐爆鸣。
“甚尔君,瞳……”
“你说晚了,她消失了。”
“……”
那人沉默了一会,又道,“还是晚了啊,那没办法啦。”
太宰治语调柔软,能听出几分无奈,“瞳酱就是这么狠心的女人,你不是早该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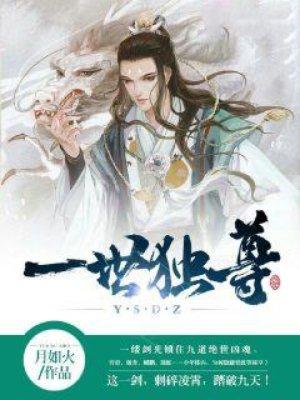
![拯救偏执反派boss[快穿]](/img/2878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