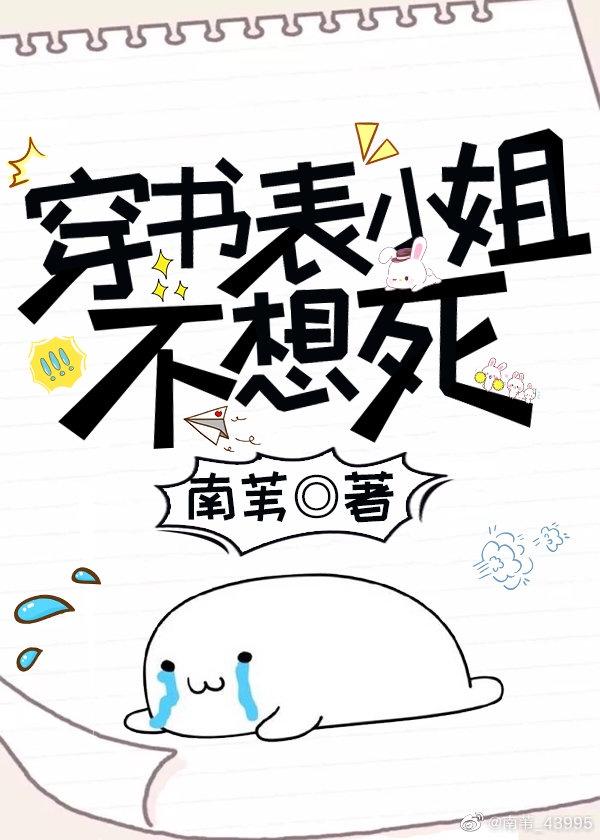笔趣阁>小青梅一直在解谜 > 算筹与谁(第1页)
算筹与谁(第1页)
牧晓有时觉得,自己亦是眼拙。
连冬将闻絮和暮药师一同送往百听阁后,刚巧将借吊唁太皇太后之名而来的陶云娴带进府中。
陶云娴走进西侧暖阁中,看到牧晓端坐在那里等她,松了一口气:“现在没事就好。殿下哭临礼时的状态,着实让人揪心。”
她暗暗猜想过牧晓是不是因天灾的事,被那神神叨叨的太皇太后叫进宫里问罪,或是下了什么手段,两方角力才弄成当时那个样子。
“云娴又推测了些什么呢?”牧晓没法和她说得太明白,向她摊了一下仍包着纱布的左手,笑了笑,“能来我府上,看来云娴在陶府中有所进展?”
“这个么,还未曾和殿下道谢。”陶云娴落座后,望着她的左手,眼睫轻颤,却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而是婉约一笑,“谢殿下当时劝我不要因家中和刘尚书之间的关系,最好不要选择隐瞒自己在平良县之事中的角色,并将我做的写进奏疏中递上去。”
“这件事的结果,和我想得全然不同。”
牧晓进宫见太皇太后时,宫中赏赐到了陶府。
陶云娴原本以为,父母会因她擅作主张插手这件事大发雷霆。
风声传到他们耳中,不出她所料,确实如此。
不过,在几个时辰后,宫中嘉奖到来,彻底掀翻了他们的态度。
陶云娴接旨后松了一口气,心道圣旨在手,父母就算再不满,也不能打落圣旨或让她带着嘉奖立马禁足或跪祠堂。
她转过身,看着父母从震惊、无措,到嘴唇无声开闭、颤抖,一口气卡在胸中,像被迎头痛击般往后倒退几步,然后突然泄了气,一言不发回屋去。
她仍是陶家的大小姐,但自此之后,不再任他们搓扁揉圆。
“原是我在乎的太浅。”陶云娴怅然道,“生长在陶府,原以为讨得父母欢心,就可过得舒心些;向他们展示自己能找到出路,就能打消他们口中对我未来的忧虑。”
“现在想想,他们说的‘为我着想’,不过是强迫我按他们既定规划走的托词罢了。”
若是真的为她心焦,为何她在平良县突然断了音信时,一日一日拖延,一日一日踟蹰不前,让云鹤气急到直接趁入宫伴读,去求皇子?
在婚事上寸步不让的是他们,为了婚事一唱一和、威胁她要向宫中请旨的是他们——但婚事比她的安危还重要么?真的遇到难题,他们的说一不二,他们的坚定果决,他们展现给她的手眼通天、无所不能呢?
都化作正在燃烧的一纸飞灰,随风散了。
原来对父母所作所为释怀的那刻,是信任崩塌的瞬间,是窥见他们亦懦弱无力的瞬间,
原来世间有这么多破局之法,不只是逃避和妥协这两种。
她不想妥协,便只是想借平良县相助逃到昭灵公主这里,求一时安定平静。
什么嘉奖之类,她完全没有想过——这是她尽自己绵薄之力就可得到的么?这是女子可获得嘉奖的方面么?
父母口中用来胁迫她、恐吓她的“宫中意向”,也被从她头上挪开,让她看到了不同以往预期的一面——婚嫁是重,但重不过朝中事务,重不过民生难题,重不过宫中人眼里的利与忠。
宫中不会吝啬这点赏赐和嘉奖,但这东西只要一点,就能让她的日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谢不必。我只是原原本本叙述罢了,不然还能欺君不成?原是我该谢你相助,免去了不少麻烦。”牧晓神色温和地看着她,“至于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不便多言。不过,就如平良县那山,不论塌与不塌,都不影响它在那处真真实实地存在过——为当地带来过富饶,也带来过灾祸。”
崩塌,可以是结果,是过程,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但从来不会成为佐证“过往即虚无”的证据。相反,每一次崩塌都在诉说,诉说过往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真真实实地存在。
心中掉落的碎石能将人砸痛,本就证明了其中蕴含的重量。
牧晗与陶郎中在京中清名甚远。为官清廉、明断是非,家中勤俭和睦,从不吝对他人出手相助;不求回报、不追名利,安稳自得。
牧晗的成名之举,是当年先帝登基之初的“三辞封赏”。
她自言庸常,在旧朝畏缩不敢反抗,在新朝建立过程中未有寸功,既然从未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光凭其父与先帝为亲兄弟便获封,实在有愧良心、有愧牧氏立身之道。
有人暗指她虚伪搏名,牧晗从来一笑而过。平日除了必须要出席的场合,她从不带陶云娴和陶云鹤接触皇室中人。
即使是陶云鹤被召为皇子伴读,也是天天耳提面命他,不能因此自觉高人一等,不能因此产生一步登天的妄想,要安安心心好好读书,端端正正好好做人。
在她眼中,一时风头无两必招致灾祸。功成名就、封侯拜相固好,却不是他们该享有的。能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日子过舒服,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