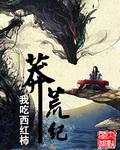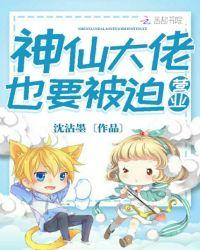笔趣阁>夫君死而复生了 > 150156(第7页)
150156(第7页)
方盈赶忙答应,带着四姐妹告退,直到走出正院,才想起来,悄悄问高氏:“怎么没提设灵堂?”
高氏也悄悄道:“在外亡故者,灵柩不能入京,要设也是在城外设灵棚。”她停了停,又接道,“兴许是想直接送回蜀中。”
也是,既然不能入城,还得回蜀中安葬,何必绕这一圈?不如直接从夏州回蜀中。
方盈带孩子们回去,先把她们安顿在鸿儿房中,鸿儿不知出了何事,还很欢喜,怀芸却隐约听见家里有丧事,一张小脸都吓白了。
叔父伯父过世,孩子们都要戴孝,方盈便缓缓说了实情,鸿儿听不懂,最先发问:“过世是什么?”
方盈揽住女儿,问她:“你记不记得爹爹说过,你还有一位大伯?”
“嗯,爹爹说大伯去地下了。”
方盈点头:“对,三伯跟大伯一样,也去地下了。”
鸿儿没见过大伯,三伯却是见过的,疑惑道:“三伯不是去做官了么?怎么又去地下了?”
方盈也想知道,好好的去当官,怎么最后饮酒把自己饮死了?
这个疑问,到傍晚纪延朗回府,又有了另一番解答。
“夏州奏报,只说三哥与党项人都头有私怨,营指挥设酒说和,也就是那刁奴口中的前一晚斗酒,奏报中说三哥因醉得不省人事,被党项人嘲笑,心有不甘,私下又约了斗酒。
“父亲把吴二叫来,说我们已经看到夏州奏报,让他重说一遍,这刁奴竟说他是一片忠心,为了三哥身后名才那般说的。”
纪延朗轻轻一拍几案:“我当日真不该逗引他去。”命丢了不说,还丢尽纪家脸面。
方盈抬手轻抚他肩背,劝道:“这怎能怪你?你也是望着三伯好,才让他去的。”停了停,又问,“那丧事呢,到底如何办?”
“父亲叫我迎了灵柩,直接扶棺回蜀中落葬,他已让五哥给二哥和四哥都写了信,等他们到洛阳,再同五哥一道陪三嫂和侄儿们回蜀中。”
纪延朗轻轻一叹:“父亲很是失望,他本以为三哥这回真改了的。”
“不追究党项人了么?”
“夏州已经按军法处置过了,营指挥降级留用,几个党项人都头处以杖刑,夏州知州还给拨了赙金。父亲虽然不满,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让党项人给三哥赔命。”
方盈看着时候不早,没再多问,只嘱咐纪延朗路上不要急,天寒地冻的,保重自己身子为要。
纪延朗口中答应,当晚早早歇下,第二日一早穿上孝服,拜别父母,带人出城,赶往夏州。
府中安氏在见过吴二后,就病倒了,纪延昌生母贺姨娘,听闻三郎没了,日夜啼哭,也把自己哭病了,直到纪延庆回府,亲自去安慰了贺姨娘两回,她才渐渐病愈。
安氏虽还病恹恹的,却也不得不挣扎起身,带着长子怀冲、庶子怀顺,与纪延寿三兄弟一道启程,回蜀中为丈夫操办丧事。
纪光庭告了几日假,直等到送走他们,才返回镇州驻地——
作者有话说:“都头”是一个官职,大概管100军士的样子。
然后兄弟之间,包括父母为非长子,都是服“齐衰不杖期”,“不杖”指在丧期内不手持“哭丧棒”。
赙金类似于丧葬费。
最后是死在城外或者外乡的人,一般灵柩都是禁止入城的,尤其都城,除非有皇帝特旨(比如红楼梦里的贾敬),否则只能在城外设灵棚,或者像尤氏一开始布置的那样,直接停灵在寺庙里。本文这个老三显然不具备资格。
第154章
纪延朗一行直到二月中才回到洛阳府中,此时太子都已率同留守东京的官员到了洛阳。
“怎么瘦了这么多?”夫妻二人刚从李氏院里出来,方盈便忍不住心疼地问。
纪延朗摸了把脸:“你不说我都没觉着。”确实凹下去,没有肉了,“可能来回奔波的,三千多里地呢,没事,养养就长回来了。”
“我看三嫂也瘦得狠了。”安氏本来两颊圆润,是个圆团脸,现在瘦得尖下巴都出来了,身上衣裳更是空空荡荡,叫人看着便心中叹息。
纪延朗点头:“这一路三嫂都是强撑着。”
二人说着话回到房中,方盈照例伺候他沐浴,谈起别后诸事。
“太子入京,你跟太子妃也终于能通消息了吧?”纪延朗问。
“是啊,可算是通消息了,你知道么?原来太子妃去年也有孕了,赶在腊月二十八生的,是个小郡主。”
纪延朗惊讶:“这么大的喜事,怎么年节里一点都没听说?”
方盈道:“腊月二十八才生产,第二日就是除夕,消息哪有那么快传来?”
纪延朗恍然:“是啊,初五咱们就接到丧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