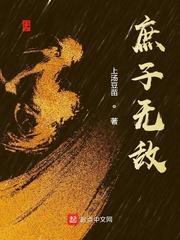笔趣阁>宋檀记事 > 1717(第3页)
1717(第3页)
她停顿了一下:“你可以带走一段代码,但带不走那个半夜惊醒跑去看苗床的女人。”
年轻人红了眼眶,当场撕毁了拷贝U盘。
正月十五,元宵灯会。
村民们扎了七盏大灯笼,形状各异:有药草模样的,有田犁造型的,还有一盏做成陶瓮样式,象征“归种计划”。灯笼底下挂着谜语条,其中一条写着:
>“生于黑土无人识,掘之千载亦芬芳。打一作物。”
答案是:黄精。
当晚,宋檀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是那位匿名订购百份黄精的客户,真实身份终于揭晓??竟是曾公开质疑“云桥模式”的某位知名财经评论员。他在信中写道:
>“我曾以为你们是在表演农业。直到我去了一趟西北,看到沙漠边缘的移民村,那里的合作社照搬你们的模式失败了。他们缺的不是技术,不是资金,而是你们那种‘宁愿少赚也要说实话’的底气。
>我终于明白,云桥不可复制,因为它根植于一群人的选择,而非一套方案。
>所以,请允许我重新介绍自己:
>不再是批评者,而是学习者。”
宋檀将这封信打印出来,贴在农事日志的首页。旁边夹着一张新拍的照片:早春的第一场细雨落下,几个孩子穿着雨靴在药圃里追逐蚯蚓,笑声穿透雨幕。
二月初二,龙抬头。
春雷始鸣,蛰虫出动。宋檀宣布启动“共生试验田”项目:在同一地块混种黄精、玉竹、金银花与野大豆,模拟原始林下生态系统,减少人工干预,观察自然调控能力。
“我们过去总想着掌控一切。”她在启动仪式上说,“但现在,我们要学会退后一步,听听土地自己想长出什么。”
就在当天下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位白发老太太拄拐而来,自称姓林,从江西徒步两个月才找到云桥村。她带来一包种子,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失落地黄”,曾在战乱年代救活整村饥民,后来因产量低被淘汰,仅靠族中老人秘密留存。
“我知道你们不做商业育种。”老太太颤巍巍地说,“但我实在找不到别处可托付了。”
宋檀接过布包,打开一看,种子干瘪灰暗,毫不起眼。可当她指尖触到那一粒粒微小的生命体时,心头竟猛地一颤??仿佛某种久远的血脉在苏醒。
她郑重收下,当场立碑为证:
**“此田今日起休耕三年,专育林氏地黄。非为利,只为不忘。”**
夜深人静,宋檀再次翻开农事笺,执笔写道:
【二月初二,龙抬头。
今日无晴无雨,唯有信至。
有人千里送种,如古人托孤。
我知这世界越来越快,记忆如沙漏倾泻。
可总得有人蹲下来,用手拢住那些即将散尽的火苗。
我不是救世者,也不指望改变大局。
我只是不愿在回首时,发现自己也曾袖手旁观。
春来了。
尽管它脚步踉跄,带着伤痕,
可它终究,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