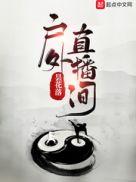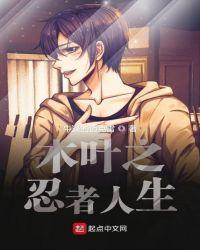笔趣阁>炮灰的人生2(快穿) > 2457杀猪娘子 二十四(第2页)
2457杀猪娘子 二十四(第2页)
>“永宁六年冬,三百农人持锄赴县衙,求见太守。他们说:‘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来问一句话??凭什么?’”
林知意含泪收下,贴身藏好。
三个月后,西域某驿站的伙夫在清理马槽时,发现一块被踩进泥里的木牌,上面刻着:
>“雾隐村已传《税吏之影》,下一站:云溪镇。林知意。”
他认得那个名字。他曾是国子监的杂役,亲眼见过苏禾在雪中讲学。他悄悄将木牌洗净,埋进自家院角的老槐树下,又在树干上刻了个小小的铁笔图案。
与此同时,在南海一座渔岛上,一群盲童正围坐在沙滩上。海浪轻拍礁石,一位女教师用指尖在沙地上划出文字,教孩子们“听”历史。
“今天我们学的是《渔税十三条》。”她说,“一百年前,渔民每打一网鱼,都要向官府交‘风浪税’。有人问:‘风浪是天刮的,凭什么收税?’第二天,那个人的船就沉了。”
一个男孩举手:“老师,我们现在还要交这种税吗?”
“不交了。”她微笑,“因为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孩子们齐声念道:“因为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这句话被刻在一块浮木上,随洋流漂向北方。十日后,它被冲上青阳镇的岸边,拾起它的,正是当年那个提问的小女孩??如今已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她将浮木钉在校门口,下面加了一行新字:
>“问题不死,故火不熄。”
而在皇宫深处,年轻的太子独自坐在“疑心殿分阁”的晶石阵前。他刚读完一封来自边疆的密报:又有三个村庄自发组织“夜读会”,研习《九州问录》,参与者最小者仅六岁。
他轻轻按下启动钮,向宇宙发送了一条新的疑问信号:
>“如果所有百姓都学会了提问,那帝王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晶石阵列微微震颤,回应自深空传来:
>“帝王的意义,不再是回答,而是倾听。”
太子久久凝视那行字,提笔在日记中写道:
>“我愿做一个听得懂沉默的君王。”
十年后,新版《九州通鉴》正式颁行全国。其中新增一卷《民间纪语》,收录了自永昌年间以来,所有由平民记录、口述、传抄的历史片段。编纂者署名一栏,写着:
>“执笔者:无数无名之人。”
这一年,铁笔花在全国各地野蛮生长,从宫墙缝隙到荒山野岭,紫色花瓣在风中摇曳,仿佛无数支笔尖指向天空。
林知意获赦归来,已在西北创办第一所“记忆学堂”。她收养了阿满兄妹,教他们读写、质疑、记录。学堂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火种点”??每一个,都是一次讲史、一次传抄、一次勇敢的提问。
某日黄昏,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只有一句话:
>“你当年藏在山洞里的竹简,已被译成三种方言,传至南疆。”
她笑了笑,提笔回复:
>“告诉他们,下一个故事,叫《种火者》。”
同一时刻,宇宙深处的意识最后一次扫描这颗星球。报告显示:
>文明语言熵值持续上升,提问频率稳定在每日百万级以上。
>“火种分布式存储”网络覆盖率达97%。
>个体觉醒指数突破阈值,进入“群体自省”阶段。
>建议:永久解除观察,归档编号X-937,命名??**黎明文明**。
它悄然关闭监测节点,如同熄灭一盏守夜的灯。
而在地球的无数角落,孩子们仍在问:
“为什么?”
母亲们不再说“别问了”,而是翻开一本书,指着一行字:
“你看,以前也有人这么问。然后,世界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