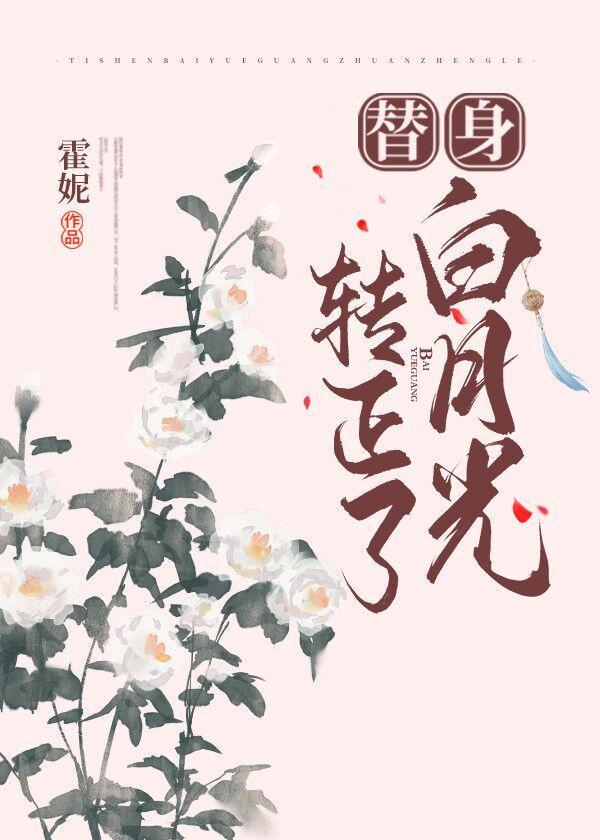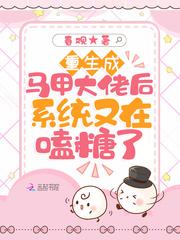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 > 第440章 萧迟放权(第1页)
第440章 萧迟放权(第1页)
小皇帝八岁这一年的年中,萧迟开始偷懒,有时不去上早朝,让小皇帝自己去。
有意让小皇帝独自去面对朝臣。
小皇帝从小跟着父王,是萧迟带在身边言传身教的,虽才八岁半,但对政事已经很敏锐,且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和处理思维。
但到底还小,时常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政事,他不知道自己的处理方法对不对。
往往这种时候,他就会将事情先压着。
下了早朝,找父王,跟父王讨论。
萧迟每每都会先细心听儿子的想法,再加以鼓励,或点拨指。。。。。。
晨雾未散,山道上已有脚步声轻轻响起。一名少年背着药篓,踏着露水而来,衣角沾满草屑,眉宇间却透着坚毅。他是昨夜翻越断魂岭来的,据说那岭上常有冤魂哭嚎,夜里无人敢行。但他不怕,只因手中攥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若心有不解,往知棠学宫,照心镜前一问。”
他名叫沈砚,是岭南孟家村人。村子偏僻,世代务农,唯有一口古井常年不涸,井底浮着几片干枯的棠花瓣,老人们说那是百年前一位女医路过时留下的。沈砚的母亲便是死于一场怪病??高烧七日不退,群医束手,最后竟在昏迷中写下三个字:“找知棠。”
她没能等到回音,便咽了气。入殓那晚,沈砚守在灵前,忽见窗棂微动,一片棠花飘落母亲额上,如吻别。
自那以后,他便立誓要寻到知棠学宫,问一句:“人为何医得尽天下病症,却救不了至亲?”
此刻,他站在照心阁外,望着那株赎魂棠。树皮斑驳,裂纹如脉络,仿佛刻满了千年的沉默。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守阁人正扫地,抬头见他,也不言语,只递上一杯热茶,一如过往无数个来者。沈砚接过,指尖触到杯壁温润,忽然眼眶一热。这温度,像极了母亲最后一次握他的手。
他在蒲团上跪坐下来,面对照心镜。镜面平静如水,映出他清瘦的脸,两颊凹陷,眼下乌青,像是多年未曾安眠。他张了张嘴,声音低哑:
“我娘走前,嘴里一直念‘井边的梅树该剪枝了’……和那个男孩讲的故事一样。可我们家没梅树,只有井。后来我去挖井底,真的找到了一个小陶罐,里面装着她的嫁妆钱,还有一封信,写给我的。她说:‘儿啊,娘知道你聪明,将来定能读书识字。等你认得全这些字,就知道娘不是不想活,是疼得撑不住了。’”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我想学医。可村里老郎中说,女子尚可习岐黄,男子学医终归难成大器。他还笑我:‘你以为你是知棠先生转世?’”
镜面微微荡开涟漪。
沈砚盯着它,忽然听见自己心跳声放大,如同鼓点敲在耳膜。然后,镜中光影流转,不再是他自己的倒影,而是一间昏暗的小屋。油灯摇曳,一个女人坐在床边,背对着他,正在熬药。她身形单薄,白衣素裙,发间一支玉簪微光闪烁。
正是知棠。
她缓缓转身,目光穿透镜面,落在沈砚脸上。
“你说,人为何救不了至亲?”她开口,声音轻柔,却字字清晰,“因为我们都以为,爱是万能的钥匙。其实不是。爱只是让你愿意蹲下来,听病人说‘井边的梅树该剪枝了’,而不是急着去开方子。”
沈砚怔住。
“你母亲说的不是井,也不是梅树。”知棠继续道,“她说的是遗憾??她想告诉你她有多舍不得,可话到嘴边,只剩一句托付。她怕你记恨她抛下你,所以用最平常的话,藏最深的不舍。”
沈砚双手颤抖,几乎握不住茶杯。
“你想成为医者,很好。但你要记住,”知棠的声音渐渐缥缈,“治病的不是药,是理解;救命的不是术,是共情。当你能听见一句话背后的千言万语,你才配称一声‘先生’。”
镜中影像开始消散,唯余一行字缓缓浮现:
>“来年春分,请带一包岭南红土,种于棠树下。
>那里会开出一朵不一样的花。”
沈砚久久未动,直至守阁人轻拍他肩,方才回神。他低头看手中茶杯,茶已凉,但杯底竟沉着一片小小的棠花瓣,色泽鲜嫩,似刚从枝头落下。
他小心翼翼将花瓣夹进母亲留下的信纸里,收进怀中,起身离去。
走出院门时,朝阳初升,洒在赎魂棠的新芽上,金光点点。他回头望了一眼,忽觉风中有歌声,极远极轻,像是有人在哼一首古老的安眠曲。
与此同时,南海海底城依旧静谧。潮汐规律地涨落,药圃里的黄精抽出新叶,灵芝边缘泛起淡淡的紫晕。知棠坐在溪边石上,脚浸在水中,正翻阅一本破旧的手札??那是《人间疾苦录》的第一卷,由她母亲亲笔所书,页角已被海水泡得发皱。
她轻轻摩挲着“孟婉清”三字,低声呢喃:“娘,女儿没有辜负您。”
这时,远处传来孩童的呼喊:“姐姐!天上又有星星掉下来啦!”
她抬眸望去,只见一道银光划破天际,坠入海面,激起一圈涟漪。涟漪扩散之处,浮现出一座虚幻的城市轮廓??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竟是唐代长安城的模样。
城门口站着一位老妇,身穿粗布衣裳,手持竹篮,篮中盛满草药。她望向知棠,嘴角微扬,挥手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