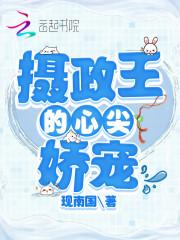笔趣阁>影视编辑器 > 第129章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第3页)
第129章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第3页)
苏宁没有反抗。他当着众人的面,将铁盒、信件、胶片一一递出,神情坦然。
“我可以跟你们走。”他说,“但请回答一个问题:周承恩,真的是烈士吗?”
对方沉默良久,终是避开视线:“此事正在核查中。”
“那就够了。”苏宁点头,“至少你们也开始查了。”
三天后,《潜伏》剧组宣布暂停拍摄,全员接受背景审查。网络上关于预告片暗藏玄机的讨论愈演愈烈,民间技术爱好者自发组织破解行动,短短四十八小时内,已有十余个国家的媒体发布“中国新剧揭露建国前夕谍战黑幕”的专题报道。
而苏宁本人,则被带入一处保密基地进行问询。
审讯室无窗,灯光惨白。对面坐着两位老者,一位身穿军装,另一位戴着眼镜,面容熟悉。
“你不该碰这段历史。”军装老人叹道,“有些人死了,就应该永远死去。”
“可有些人活着,却比死人更可怕。”苏宁直视对方,“比如一个本应牺牲的叛徒,如今坐在权力顶端,决定哪些故事能讲,哪些必须消失。”
眼镜老人缓缓开口:“你知道重启‘白鹭计划’意味着什么吗?不是拍一部电视剧那么简单。你在唤醒一场尚未终结的战争。”
“那正好。”苏宁冷笑,“我也想看看,这场仗,到底谁才是最后的幸存者。”
就在此时,助理匆匆推门进来,在首长耳边低语几句。老人脸色微变,看了苏宁一眼,起身离去。
半小时后,苏宁被释放。
门口,陈晓君等在车旁,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刚接到消息,周承恩主动申请辞去所有职务,正在配合组织调查。另外……国家档案局发布公告,将于下周解禁一批1940年代地下党活动资料,首批名单中,包含了‘白鹭’苏振国的完整事迹。”
“还有呢?”苏宁问。
“还有……”她哽咽了一下,“民政部门正式更正你父亲的死亡性质:由‘失踪追认’改为‘执行任务期间被捕牺牲’,并补发烈士证书。”
风拂过脸颊,带着春日的暖意。
回到老洋房那天,已是清明前夕。工人们正在院中竖起一座小型纪念碑,上面刻着几个朴素的大字:
**致那些未能归来的潜伏者**
苏宁站在碑前,点燃三支香,轻轻插进泥土。
身后脚步轻响,林婉不知何时到来,手中捧着一只小木匣。
“这是我母亲留下的。”她低声说,“她说,等你找到真相那天,就交给你。”
打开木匣,里面是一枚铜铃,铃舌上缠着红绳,正是童年记忆中的那只。
“原来你真是……”苏宁望着她。
“我是‘麻雀’的女儿。”她微笑,“也是你父亲最后一个联络员。他没死,但他再也无法回来。而我,替他守到了今天。”
两人并肩而立,望着夕阳洒落在老洋房的砖墙之上,宛如镀金。
当晚,苏宁更新微博,附上一张照片:铜铃悬挂在阳台,随风轻摆,发出清越之声。
配文只有四个字:
**他回来了。**
夜更深了。
城市灯火依旧璀璨,如同永不熄灭的星河。而在某间隐蔽的房间里,一台老旧电视正无声播放着《潜伏》预告片。屏幕前,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摘下帽子,对着画面深深鞠了一躬。
他的左手,缺了无名指的一节。
窗外,雨悄然落下,打湿了墓园里一块新立的石碑。碑上名字模糊不清,唯有下方一行小字清晰可见:
**此处安息之人,曾以一生沉默,换山河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