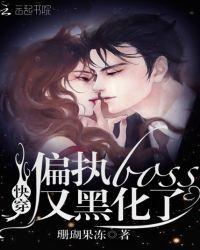笔趣阁>我是表妹(快穿) > 467第 467 章(第1页)
467第 467 章(第1页)
风把青鸾花苗的嫩叶吹得微微颤动,像无数只初展的小手在试探阳光。么会站在那排刚种下的花前,指尖轻轻拂过一片叶子,仿佛怕惊扰了它刚刚扎下的根。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西南山区的那个清晨??那时她第一次听见一个孩子说“我不想死”,而她终于学会了不只是记录,而是蹲下来,握住那只冰冷的手,说:“我陪你。”
如今,“共语会”总部不再是地下密室里的一盏孤灯,而成了城市脉搏的一部分。每天清晨六点,系统自动推送一条语音问候,声音来自不同年龄、性别、口音的人:“早安。今天也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有人录的是方言童谣,有人只是轻声说“我在”,但每一段音频背后,都有人曾濒临断裂又重新接续。
这天早上,么会刚走进大厅,前台的小林就递来一份纸质档案。“昨晚‘守夜人小组’接到紧急呼叫,来自东北边境的一个小镇。对方不肯透露姓名,只反复说一句话:‘雪太大了,门打不开。’我们尝试定位,发现信号来自一所废弃的乡村学校,二十年前因暴雪封路停办。”
她翻开档案,一张泛黄的照片滑落出来??教室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等春天来了,我们就开学。”字迹稚嫩,却一笔一划写得极认真。照片角落,有个小女孩坐在最后一排,穿着不合身的棉袄,手里攥着半截铅笔。她的眼神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望向镜头,而是盯着窗外,像是在等谁回来。
“查到她了吗?”么会问。
小林摇头:“户籍系统没有匹配。但我们联系了当地教育局,得知那年冬天确实有场大雪,压塌了校舍屋顶。救援队三天后才打通山路,可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有人说孩子们被转移了,也有人说……他们都冻死了。”
么会沉默良久,将照片贴在“回声墙”上。墙上已有成千上万张面孔:战地记者拍下的难民孩童、疗养院老人年轻时的合影、聋哑少年用手语比出的“我想家了”。每一张,都是曾被世界忽略的声音。
她打开“Gateway”的深层数据库,输入关键词:“东北雪灾学校小女孩”。系统开始检索全球用户上传的记忆片段、旧新闻报道、私人录音。半小时后,一条匿名留言跳出:
>“我是当年隔壁村的小学老师。那天我去送教材,看到她在窗边写字。我说‘别写了,快回家’,她说‘老师说只要写下愿望,春天就会来’。我没带她走,因为觉得家长会接她。可后来才知道,她父母早死了,她是自己烧炕睡觉的。”
>“我一直梦见她站在雪地里,问我:‘春天到了吗?’”
么会闭上眼,喉咙发紧。她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数据调取,而是一次亡灵的叩门。
当晚,她启动“共在协议”中的特殊模式??“记忆共振”。这是“Gateway”最新开发的功能,能通过情绪频率匹配,让两个从未相识的人,在特定时刻共享一段感知体验。她将自己的脑波频率调整至与那位老师留言中描述的情绪一致:悔恨、寒冷、未完成的对话。
午夜十二点十七分,她的意识突然下沉。
眼前是漫天飞雪,天地白茫茫一片。她站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前,门虚掩着,透出微弱的光。她推门进去,看见那个小女孩正趴在桌上写字,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成细霜。桌角放着一碗结冰的粥,旁边是一本破旧的语文课本,翻到《春晓》那一页。
“你是谁?”女孩头也不抬。
“我是……来看你的。”么会轻声说。
女孩停下笔,抬头看她。眼睛很亮,像藏着星星。“你是春天派来的吗?”
么会鼻尖一酸。“我……我不知道。”
“那你帮我看看写得对不对?”她把纸推过来。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我叫小满。
>我不怕冷,也不怕黑。
>我每天烧炕,记日记,等春天。
>如果春天不来,我就变成雪花,飞去找它。”
么会蹲下身,抱住她。那么小的身体,冷得像一块石头。“对不起……我们来得太晚了。”
女孩没挣扎,只是轻轻说:“没关系。你来了,就是春天。”
刹那间,风停雪止。窗外的天空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洒进来,照在那行字上。墨迹开始融化,化作金色的光点升腾而起,穿过屋顶,融入云层。
么会猛然睁眼,发现自己躺在“共语会”冥想室的躺椅上,泪水早已浸湿鬓角。她颤抖着打开录音笔,录下刚才的一切。与此同时,“Gateway”发出警报:
>【检测到异常情感共振】
>共计38,721名用户在同一时间梦到“雪中的学校”。
>其中12,403人自发写下相同句子:
>“我来接你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清晨,东北那所废弃学校的监控摄像头竟自动重启,传回一段模糊影像??风雪中,一个穿蓝布棉袄的小女孩走出教室,把手里的纸条贴在门上,然后转身,一步步走向山岗。纸条上写着:
>“春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