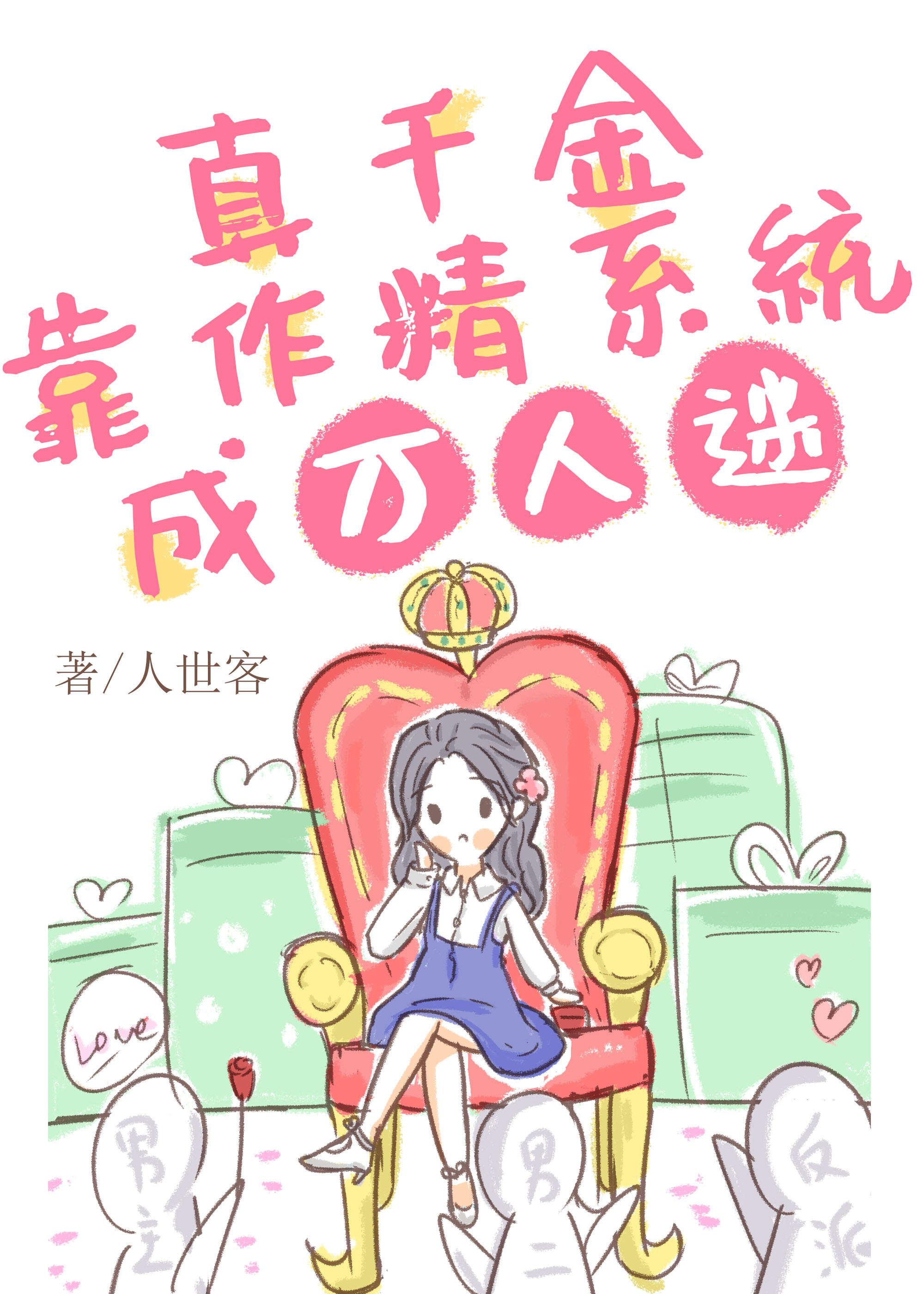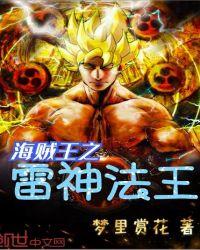笔趣阁>大雪满龙刀 > 0481三圣(第1页)
0481三圣(第1页)
一时之间,所有人心中都无比惊惧。
没想到今日之战会演变成为圣战。
圣人之战的威势恐怖绝伦,将整个神京城夷为平地也绝非是危言耸听。
仅仅是两位圣人对峙所散发出的无形威压,已让天地失色,空间凝固。
周遭无数观战的顶级强者们都感觉心脏被无形之手攥紧,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仿佛置身于万丈深海,随时会被碾成齑粉。
两大圣人的对峙,如同两座即将碰撞的太古神山,压抑得令人窒息。
空气粘稠如铅汞。
光线都为之扭曲黯淡。
雪未化尽,山谷却已不再冷。那支断笛在少年唇间低鸣,音色如初春的溪水,清冽中带着裂痕的沙哑。它不似当年陈无玖挥刀斩断律巡铁律时那般雷霆万钧,也不像米青萝焚身祭塔时那般悲壮决绝,而是一种缓慢的、持续的震动,像是大地深处某根断裂的筋脉正在重新接续。
秃毛鸡蹲在少年肩头,羽毛被晨风吹得微微鼓动,它眯着眼,仿佛在听风里的密码。“你这口气……还行。”它嘀咕,“比上一个合格,比前十个强多了。至少没把笛子当烤肉叉子用。”
少年没理它,只是低头看着手中这支残破的乐器。裂纹从笛尾蜿蜒至唇口,像一道干涸的血痕。他不知为何,在梦里听见的歌,竟与这笛声天然契合。每一个音符落下,脚下的青苔圈便轻轻一震,仿佛回应着某种沉睡的契约。
忽然,远处传来马蹄声。
三匹瘦马踏雪而来,背上各负一人。为首的是个戴斗笠的老妇,脸上皱纹纵横如刻刀划过石碑,怀里抱着一只木匣,边角已被磨得发亮。她翻身下马,脚步稳健,直奔青苔圈而来,在距离三步处停下,双膝跪地,将木匣轻轻放在雪中。
“我来了。”她声音沙哑,却清晰,“等了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声笛响。”
秃毛鸡跳下少年肩膀,绕着木匣转了一圈,啧了一声:“哟,‘缄言录’第三卷?这玩意儿不是早该烂成灰了吗?”
老妇抬头,目光如钉:“我娘临死前塞进灶膛,我扒了三天三夜才抢出来。每一字,都是用指甲刻在桑皮纸上的。她说??‘只要还有人肯读,我们就没输’。”
少年怔住。他知道这名字。《缄言录》,曾是归零殿明令焚毁的七十二禁书之首,记载了自天启元年以来,三百七十九位因直言获罪者的遗言、家书与临终证词。传说全书共九卷,每卷藏于不同隐士之后,代代口传心授,无人敢轻启。
而眼前这一卷,封皮虽旧,但边缘齐整,显然近年才重装过。
“你是……柳家后人?”少年问。
老妇点头:“柳念慈孙女。我祖父因写下‘税重民饥,非贼作乱’八字,被剥舌游街,死于冬夜。我爹活到六十岁,从未提过他名字。但我记得。我娘也记得。我们一家三代,就靠记住这两个字活着。”
她打开木匣,取出一叠泛黄纸页,轻轻铺在雪地上。风欲卷之,却被一层无形屏障挡住。纸面墨迹斑驳,但依稀可见一行行小楷,笔力枯瘦却倔强:
>“吾儿昨夜啼饿,问我:‘天上有星,地上有灯,为何家中无米?’我不能答,唯抱之泣。若世间尚有一耳愿听,此语请录之,勿忘。”
少年手指微颤。这些话,不该只躺在匣中。它们本该在阳光下被朗读,在市集上传唱,在学堂里教给孩童如何辨认“饥饿”二字的真实重量。
他抬起笛子,再度吹奏。
这一次,旋律变了。不再是抚慰,而是召唤。音波扩散开去,青苔圈骤然亮起,绿光如脉搏跳动,顺着地表蔓延而出,直指九方。数息之后,远方天际浮现九点微光??那是九座忆辉学院同步感应的回应。
秃毛鸡展翅飞起,对着天空长鸣三声。刹那间,风中响起无数脚步声。
北境来的说书人背着铜铃鼓,南荒的盲眼诗人拄着竹杖,西域商队首领解下行囊中的羊皮卷,东海渔妇捧出用贝壳串成的“海语谱”……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皆因同一征兆:忆辉植物集体震颤,叶片传出一句反复回荡的话??
**“缄言录现世,众声当归位。”**
少女的身影也在人群中出现。她已不再年轻,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依旧清澈如泉。她走到少年身边,轻声道:“你吹出了‘启封调’。这是米青萝留下的最后一式,只有真正听见沉默的人才能奏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