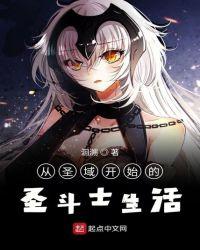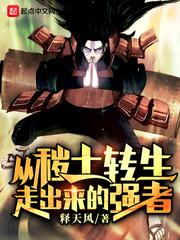笔趣阁>秦人的悠闲生活 > 第三百六十一章 巡长城的皇帝(第1页)
第三百六十一章 巡长城的皇帝(第1页)
当年章邯戍边,会经常来此地,指着远处又道:“从这里再往北走几里地会有一个草场,如今还养着不少羊群。”
听着大将军讲述,小公主也在远眺着这片荒原。
因是冬季,放眼看去其实是一片荒芜,也只有在。。。
车队东归,行至酒泉以东百里处,忽遇沙暴骤起。黄尘如浪,自天边滚滚而来,遮天蔽日,马嘶人呼,旌旗几欲断裂。随行工匠急忙以牛皮帐幕覆于御驾之上,士卒列阵成墙,背风而立,护住粮车与民夫。
扶苏策马奔至中军,见吴平并未惊慌,反而掀开车帘,凝望那漫天黄沙,眼中竟有几分欣慰之色。
“陛下,此风暴凶险异常,是否暂避?”扶苏大声问道,声音几乎被风声吞没。
吴平摇头:“不必。你看那风势虽烈,却有方向??自西北来,东南去。这正是祁连雪水融尽、春末夏初之际特有的‘走龙风’。古人谓之灾,实则乃天地吐纳。若能识其律,便可顺势而为。”
他指了指远处一道隐约可见的沟壑:“那是新修的引水渠尾端。去年章敬命人依地势开渠,将冰川融水导入屯田。今日风起,正好吹净渠面浮沙,明日水流更畅。”
扶苏怔然。他原以为风暴是祸,而在吴平眼中,竟是自然可资利用的一部分。
风势渐弱,日头破云而出。阳光洒在湿润的渠床上,泛出粼粼波光。百姓早已等候多时,提着陶罐、牵着孩童,在渠口排队接水。一名老农跪地掬饮一口,老泪纵横:“活了六十岁,第一次喝上清亮的山水!”
这一幕被记入扶苏的竹简:
>“治世者,非逆天而行,乃顺道而动。暴雨可淹城,亦可灌田;狂风毁屋,亦能除尘通渠。关键不在天象如何,而在人能否知其性、用其利。今上不怨天灾,反借天力,可谓得自然之机枢。”
三日后抵达武威,此地已成河西重镇。昔日荒芜之地,如今阡陌纵横,桑麻遍野。市集上胡商与汉人混杂交易,驼铃叮当,丝绸、香料、铁器琳琅满目。更有奇景:一排排蜂窝煤炉整齐排列,炊烟袅袅却不刺鼻,百姓称其“暖而不呛,烧一夜只需两块煤”。
扶苏走访民居,见一家五口围坐火塘边,妇人正用铜锅炖羊肉,香气扑鼻。小儿问母:“阿娘,这肉怎的这般香?”妇人笑答:“因灶里烧的是陛下赐的煤,锅是官府发的新铸铁锅,油是关中运来的菜籽油??样样都不同了。”
临行前,一位白发老妪拦住车驾,颤巍巍捧出一双布鞋:“老奴无儿无女,唯会做针线。这双鞋,是用官府分的棉花纺线、自家织布做的,求陛下收下,替老奴给边关将士穿吧。”
吴平亲自下车接过,当众穿上,笑道:“正合脚。”随即解下腰间玉佩回赠,“你是我大秦的母亲。”
老妪伏地痛哭,满街百姓随之跪拜。
当晚宿于驿站,扶苏辗转难眠。他取出水囊,发觉内里尚余半囊清水,轻轻啜了一口,凉意沁心。窗外月明星稀,远处传来戍卒换岗的梆子声,节奏安稳,一如这土地的心跳。
他提笔续写:
>“从前读《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总觉空泛。今见陛下以一玉佩换一布鞋,非作秀,而是真心视民如亲。他不必高呼仁政,只消一个动作,便让千万人明白:他们的辛劳,有人看见;他们的善意,有人珍重。”
次日启程,途经一处新建学堂。吴平临时下令停驾,步入其中。
学堂不过三间土屋,却整洁明亮。二十几名孩童齐声诵读《仓颉篇》,稚嫩嗓音穿透晨光。教书先生是个退役老兵,独臂残腿,却站得笔直。
“孩子们,”吴平温和问道,“可知道为何要读书?”
一名童子举手:“为了不当睁眼瞎!”
众人轻笑。
又一人答:“爹说,识字就能看懂告示,知道朝廷发了多少粮、哪家被征税。”
吴平点头:“说得都对。但还有一条??读书,是为了学会做人。”
他转身对随行礼官道:“传旨:凡边地私塾,每十名学生以上者,由官府供给纸笔墨砚;教师若为退伍将士,每月另加粟米三斗,布一匹。”
消息传出,老教员当场落泪,颤声道:“末将……曾为国断臂,未想今日还能育人报国。”
扶苏默默注视这一切,忽然想起咸阳宫中的太学。那里楼宇巍峨,博士云集,讲经论道,气势恢宏。可那些学问,有多少真正抵达民间?而此处粗屋陋室,一句“识字不为睁眼瞎”,却道尽教育之本义。
数日后进入陇西,地势渐高,山岭起伏。山路崎岖,车马难行。忽闻前方喧哗,原来是一队商旅被困山口,骡马负重过甚,蹄陷泥中,寸步难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