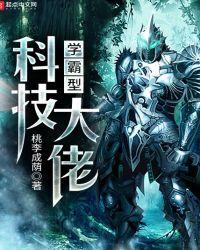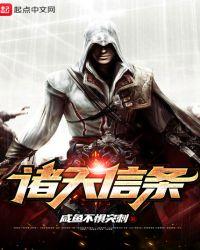笔趣阁>谁说我是靠女人升官的? > 323长公主对苏陌极度满意(第2页)
323长公主对苏陌极度满意(第2页)
可当他们伸手接过时,碗突然翻转??米粒倾泻而下,化作泥土。再抬头,那些人影开口了,声音重叠却清晰:
>“我们饿着肚子种的,你一口都没看见。
>我们冒着风雪运的,你一句都不记得。
>现在你说‘这是应得的’?
>那么,请先叫出我们的名字。”
无人能答。
梦醒时分,泪湿枕巾。
次日清晨,京城爆发前所未有的景象:数千人自发涌向郊区农田,请求加入春耕队。昔日趾高气扬的公子哥儿跪在田埂上,向老农磕头拜师;贵妇脱下绣鞋,挽起裙摆插秧;连皇室宗亲也牵牛荷犁,亲赴南苑试验田。
这场“醒雨”持续五日,波及十八省。事后查明,雨水中含有微量逆梦露与赤薯花粉混合结晶,其共振频率恰好能激活人类潜意识中的愧疚记忆。
没人知道源头何在。
但在西北一座聋哑村的祭坛上,村民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齐齐指向南方天空。他们虽不能言,却用手语打出同一个词:
**她回来了。**
阿禾死后十二年,她的身影从未出现在人间。可每当虚假再度蔓延,总有一种力量悄然觉醒??或是一场奇雨,或是一阵低语,或是一个孩童无师自通唱出的古谣。
有人坚信她是苏府意志的延续,有人说是赤薯根系编织的集体意识,也有人认为,那是文明本身在濒临腐朽时触发的自救机制。
而在敦煌石窟深处,那幅壁画中的女子面容愈发清晰,双目似睁未睁,右手轻抚大地,左手握铃半举,仿佛随时准备敲响。
某夜,守窟僧人突见壁画生光,女子指尖滴落一滴血珠,坠地即化为一颗赤薯种子。他颤抖着拾起,埋入庙前土中。七日后,薯苗破土而出,叶片背面竟浮现出一行小字:
>“别信看得见的奇迹,信那看不见的汗。”
此事传开后,三大禅寺再次联名上书,请立“真人典”。这一次,朝廷未加阻拦。
但典籍编纂过程中,无论学者如何努力,始终无法写下完整的“苏府传”。每当日暮抄录完毕,纸张必自行焚毁,唯余焦痕勾勒出一个问号。
最终,史官只得作罢,在《实录?人物志》空白页夹入一片干枯的薯叶,并题八字:
**不知其名,唯知其行。**
与此同时,南方某座荒废书院遗址中,一群少年聚于残垣之下。他们没有老师,也不识多少字,只靠口耳相传习得几句《耕心谱》残章。
其中一人问道:“如果所有人都醒了,还会有人骗我们吗?”
另一人摇头:“骗不成了。但他们会换种方式??比如告诉你‘你已经醒了’,让你停止怀疑。”
众人默然。
良久,最年幼的孩子仰头问:“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
一位少女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塞进他手里:“感觉到疼了吗?摸到粗糙了吗?闻到腥味了吗?如果你还能分辨这些,你就还没完全被骗走。”
孩子点点头,小心翼翼将泥土包好,揣进怀里。
“我要带回去给我娘看,”他说,“她说这辈子没闻清过土味,只知道饿。”
几年后,这片废墟建起一座新型学塾,不授经史,不论功名,课程只有一项:**亲手种一季粮,然后写一篇《我吃的这顿饭》**。
文章不得引用任何名人言论,不得使用成语套话,必须如实描述从播种到收获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失败、等待、虫害、失望与偶然的喜悦。
这些文章起初被讥为“村野杂谈”,可渐渐地,有人发现它们具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读完之后,人会不自觉地珍惜食物,厌恶虚言,甚至对权力产生本能般的警惕。
更奇怪的是,某些文章末尾,会出现一段不属于作者笔迹的文字,像是有人半夜悄悄添上:
>“你以为你在写饭?其实你在写你自己。”
此类现象屡禁不止,抄写员称“明明写完就收笔,次日却多出几行”。专家查验纸张,确认无后期涂改痕迹。
最终,官方只得默认其存在,并将其归类为“耕文异象”。
而在东海孤岛上,渔民曾打捞起一块漂流木,上面刻满陌生符号。经学者破译,竟是《梦语录续》早已失传的第六卷残篇,其中赫然记载:
>“梦匠之初,不在外侵,而在内许。
>其术曰:予人妄愿,养其怠心,使其视劳作为耻,视求助为荣。
>待万民皆盼天降恩泽,则真人之基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