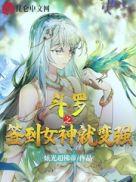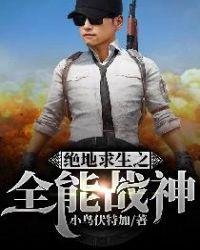笔趣阁>千禧:我真不想当大导演 > 第815章(第2页)
第815章(第2页)
当晚,他拨通李哲电话。对方接得很快,语气平静:“林老师,我知道你会找我。”
“第十七卷第三节,是不是你拿的?”
“我不是偷。”李哲声音低沉,“我是救。那段视频已经在黑市流转,有人准备把它剪成‘悲情乡村教师’系列短视频卖惨带货。我提前一步转移,是为了保原件。”
林有攸皱眉:“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告诉你们?然后呢?报警?立案?等半年调查结果出来,原片早就被肢解成一百个标题党模板了。”李哲冷笑,“你们追求真实,可这个世界根本不给真实留活路。它只认情绪,只认爆点,只认流量。”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把它做成一部交互纪录片。”李哲说,“观众可以选择不同结局:比如这位老师如果当年离开山村,命运会怎样?如果政府早五年拨款建校舍,会不会改变一切?我要用AI推演十几种可能性,让人看到结构性困境中的个体挣扎。”
林有攸沉默良久:“你不该绕开我们。”
“你们太慢了。”李哲声音疲惫,“你们坚持每一帧画面都要溯源,每一段音频都要授权,每一个名字都要打码审核。可现实是,每天都有这样的故事在消失。等你们准备好,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你就自己成了规则的破坏者?”
“我只是不想再看着重要东西无声无息地烂掉。”他说完,发来一段加密链接,“这是原始文件,完好无损。你要,拿去。但我警告你??已经有三家公司联系我买素材版权,开价最高八十万。他们要的不是真相,是要把那位老师的遗言配上煽情音乐,打上‘看完不哭算我输’的标签。”
林有攸下载完文件,确认完整性,才回复:“谢谢你守住底线。”
“别谢我。”李哲苦笑,“我只是还没彻底变成你们讨厌的那种人。”
挂断电话后,陈雯看着他:“接下来怎么处理?”
“按原计划剪辑。”林有攸打开工程文件,“但我们得加快进度。三月中旬日内瓦展览开幕前,《讲台之上》必须完成首映。”
他们开始昼夜赶工。林有攸重新调整叙事节奏,将原本分散的日常片段串联成一条隐秘的情感脉络:那些深夜批改作业的灯光,那些藏在抽屉里的止痛药瓶,那些写满学生名字却唯独没有自己生日的日历……都在诉说一种被忽视的忠诚。
二月底,影片粗剪完成。他们在老电影院组织了一场内部试映,邀请了十位乡村教师代表到场观看。放映结束,全场寂静。一位来自甘肃的男教师摘下眼镜擦泪:“这不是在拍我们,这是在替我们活着。”
第二天,新闻爆出某短视频平台出现疑似《讲台之上》泄露片段,标题赫然写着:“支教女神教师含泪告别学生,最后一吻感动全网!”画面经过变速处理,配乐哀婉,评论区已有百万点赞。
林有攸立即启动法律程序,并公开发声:“未经许可传播、篡改非虚构作品,不仅是侵权,更是对真实生命的亵渎。”同时宣布《讲台之上》提档至三月初全国公益联映,所有票房收入捐入“逆流基金”教育专项。
上映首日,全国三百多家艺术影院座无虚席。许多观众自带笔记本入场,结束后自发组织讨论会。豆瓣评分迅速飙至9。8,有网友写道:“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安静比呐喊更有力量。”
日内瓦春寒料峭,展览如期开幕。“无声档案计划”展厅以灰白为主色调,十件展品静静陈列在独立光区中。周素芬的日记本摊开在玻璃柜内,旁边播放着她晚年录音:“我不识字,但我记得每一个来找我的孩子眼睛里的光。”苗寨账本旁配有族人吟唱古歌的音频;张慧敏的准考证复印件下,循环播放着她烧毁证件那天的模拟场景??风起,纸灰飞扬,背景音是少女轻声背诵作文题。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的录音亭。第一天就有超过两百人留下声音。一位叙利亚难民用阿拉伯语讲述女儿在战火中失散的经历;一名东京上班族哽咽承认自己十年未曾与父亲说话;甚至有法国老太太录下一首童年儿歌,说:“这是我妈妈唯一教我的东西,我现在八十岁了,终于敢唱出来。”
林有攸站在展厅入口,听见各国参观者低声交谈。有人问翻译:“这些普通人为什么值得被记住?”导览员回答:“因为他们证明了,历史不该只由胜利者书写。”
回国后,他收到一封手写信,寄自云南某乡镇邮局。信纸粗糙,字迹歪斜:
>林老师:
>我是阿?,傈僳族山歌课堂的那个老师。您资助的录音设备到了,孩子们已经学会录自己的歌。昨天有个孩子唱了一首《妈妈不在家》,全班都哭了。她说她爸喝酒打妈,妈跑了三年。但她现在敢说了。
>我们把这首歌传上了‘逆流文本库’,用了您教的方法??不修饰,不说谎,只讲真话。
>您说普通人也能发声。我现在信了。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一群孩子围坐在火塘边,举着手机合唱,脸上带着羞涩却坚定的笑容。
林有攸把信贴在办公室墙上,旁边是他写下的那句话:“所有微小的坚韧,都是时代的回声。”
清明前夕,LINStudios迎来一位特殊访客??张慧敏。她穿着朴素的蓝布衫,手里抱着一个木盒。
“我来看看您。”她说,“顺便,把一样东西还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