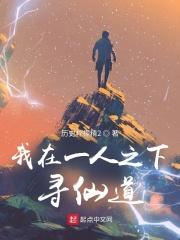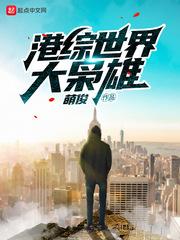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大隋刚登基,你说这是西游记 > 第486章 大运河或许是个陷阱(第3页)
第486章 大运河或许是个陷阱(第3页)
自此,“拾字童”陈九被授“守灯辅童”之职,虽无正式名分,但每逢月圆之夜,皆由他主持“夜誊课”,带领百名少年誊写民间投递的善念纸条,并择其至诚者,镌刻于新生碑上。
百姓称之为“续光行动”。
然而,风波再起。
某日,一名僧人自五台山而来,手持金钵,宣称奉佛旨降谕:“凡俗人妄自称光,亵渎天理!唯有皈依我佛,方可得渡。”
他登高宣讲,言辞激烈:“你们供奉的不过是一堆石头和火焰!真正的救赎在经文中,在寺庙里!不要再被这些虚幻仪式迷惑!”
起初响应者寥寥,但随着战乱频仍、灾荒蔓延,越来越多百姓开始动摇。有人焚灯改拜佛像,有村撤碑改建庙宇,甚至连部分守灯童子也开始偷偷诵经。
执灯官紧急召开大会,商议对策。
有人主张严惩谤灯者,有人建议请高僧辩经,更有激进者提议封锁寺院。
唯有陈九沉默。
会议结束当晚,他独自登上共光台,坐在陶灯旁,手中摩挲着那只铜铃。
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信仰之争。这是“黯”的又一次化身??它不再否定光明,而是试图垄断光明:你说光重要?好啊,那就只能按我说的方式才有光。
这才是最危险的侵蚀。
他闭目思索良久,忽然起身,走向那位来自五台山的僧人暂居的客栈。
僧人正在打坐,见他进来,冷笑:“你也来求渡?”
陈九摇头:“我是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小时候,有没有人对你好过?”
僧人皱眉:“何出此问?”
“回答我。”陈九目光平静,“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在你饿的时候给你一口饭,在你冷的时候给你一件衣,在你被人欺负时站出来护你?”
僧人怔住,片刻后低声道:“有……是我村里的王婆婆。她给我吃过红薯,还在雪天让我睡她家灶房。”
“她信佛吗?”
“不信。她说她是‘守灯人家的女儿’。”
陈九笑了:“那你口中唯一的救赎之路,她并不走。可她对你做的事,是不是救了你?”
僧人语塞。
“如果你今日能站在这里讲经说法,是因为当年那碗红薯、那个灶房。”陈九轻声说,“那么,请你告诉我??是王婆婆给你的温暖虚假,还是你现在宣扬的真理虚假?”
僧人浑身剧震,额头冷汗涔涔。
“我不反对你信佛。”陈九转身欲走,“但我反对你说‘只有你能带来光’。因为光从来不止一条路。它可以是一句经文,也可以是一碗汤;可以是一座庙,也可以是一盏灯;可以是菩萨低眉,也可以是凡人伸手。”
他停顿片刻,回头道:“你若真懂慈悲,就该知道??百花齐放,才是春天。”
三日后,僧人主动前往共光台,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金钵置于陶灯前,双手合十,深深一拜。
“贫僧错了。”他说,“我执于形式,忘了本心。真正的佛法,不在排斥他人,而在体察众生之苦。”
他自愿加入“夜巡队”,每晚提灯行走于贫民窟,为病者送药,为孤老梳头。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答:“我在还王婆婆的债。”
此事传开,民心复归。那些曾动摇的人,重新点燃纸灯;那些曾拆除的碑,被村民合力找回,擦净重立。
而陈九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孩子们传唱的新版《心灯童谣》里:
>“风吹灯不灭,
>雪压枝不折。
>有个拾字童,
>把光种成河。”
岁月悠悠,春去秋来。
二十年后,一场大疫席卷南北。朝廷束手,医者避逃,城门紧闭,饿殍遍野。
危急时刻,共光台发布“燃灯令”:凡愿逆行赴疫区者,可在“心启碑”上留名,不论成败,皆视为守灯之人。
响应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