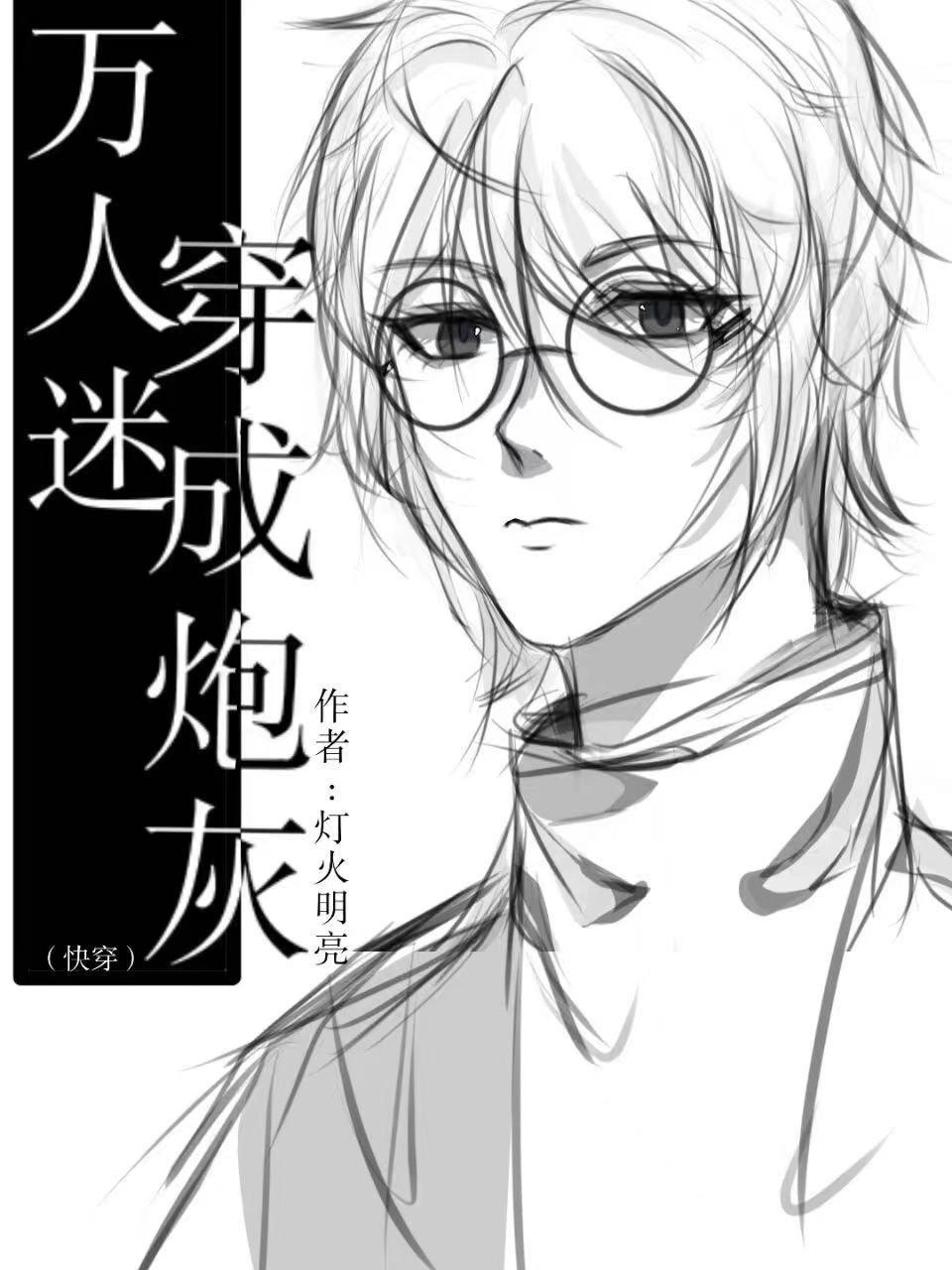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05章酿成大祸(第3页)
第605章酿成大祸(第3页)
“我这一生,都在研究如何让人‘听话’,却从来没有好好听过一个人说话。”他苦笑,“直到遇见你们,我才学会闭嘴。”
阿岩轻轻握住他的手:“你现在听得很好。”
那一夜,他们聊到很晚。江慎行讲起年轻时的一个梦??他曾幻想建造一座“终极和谐之城”,所有人都思想统一,没有争执,没有痛苦。可现在他明白了,那样的城市,不过是精致的坟墓。
“差异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理解。”他说,“就像雪,每一片都不一样,但它们一起落下时,却能让大地变得纯净。”
第二天清晨,阿岩准备离开。江慎行送他到门口,忽然说:“替我看看那口井。”
阿岩一怔:“哪口井?”
“青海湖小学后院的那口古井。”江慎行目光深远,“那是我当年埋下第一枚心印原型的地方。它不该只是传说,它该继续响。”
阿岩郑重地点头:“我会的。”
回到青海湖,已是春末。校园里的槐花开得正盛,香气弥漫。阿岩带着工具来到古井旁,小心翼翼清理淤泥和落叶。当他用长绳吊起井底一块青石时,发现石头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愿此心印,始于倾听,归于爱。”**
那是江慎行年轻时的笔迹。
阿岩抚摸着那行字,久久不语。
当晚,他召集全校师生,在井边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没有演讲,没有音乐,只有十六个人围坐一圈,轮流把手贴在井沿上,闭眼静默十分钟。
轮到李小满时,他颤抖着伸出手。片刻后,他的眼睛突然睁大,嘴唇微动。
“我……听见了。”他喃喃道,“爸爸在说……对不起。”
全场寂静。
阿岩轻轻抱住他:“他听见你了。”
从此以后,每逢月圆之夜,总会有孩子自发来到井边,许愿、倾诉、聆听。有人说井底藏有微型共振装置,科学家来检测过无数次,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电子设备。唯一能确定的是??每当有人真心想要被听见,那口井,就会回应。
十年后,联合国设立“全球倾听日”,定于每年春分。这一天,全世界暂停所有喧嚣的城市噪音,从纽约时代广场到东京涩谷,从巴黎香榭丽舍到北京长安街,所有喇叭、广告屏、广播统统关闭。
取而代之的,是十分钟的全球寂静。
十分钟后,第一声响动,往往来自某个孩子吹响的竹笛,或是一位老人轻声哼唱的童谣。
媒体称这一天为“地球的呼吸”。
阿岩已年近三十,依旧清瘦,眼神却更加沉静。他不再四处讲学,而是定居在青海湖畔,创办了一所“回响学校”,专门收容那些因创伤失语、被社会遗忘的孩子。他教他们写字、画画、种花,最重要的是??教他们如何听懂自己,也听懂别人。
策勒偶尔会来住几天,带来各地的故事。他在非洲记录部落鼓语,在北极拍摄极光下的歌声,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低语》的摄影集,扉页写着:“献给所有未曾发声的灵魂。”
李婉和聆搬到了学校附近。聆已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用手语和触觉帮助聋哑儿童感知情感。她的学生曾集体创作一部手语剧,名叫《听不见的声音》,在全球巡演时感动无数观众。
江慎行终老于昆仑山下。临终前,他将毕生笔记交给阿岩,只留下一句话:“别让技术再次成为高墙,让它做桥梁就好。”
葬礼那天,没有哀乐,没有致辞。阿岩站在铜铃塔前,带领三千五百名觉醒者,共同进行了一次十分钟的寂静仪式。
结束后,风掠过塔檐,响起了一声悠长的叮??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清晰,都温柔。
多年后,有学者研究发现,自“回响时代”开启以来,全球自杀率下降76%,战争冲突减少83%,人际信任指数持续上升。但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何越是偏远闭塞的地区,心印共鸣反而越强。
直到一位人类学家提出假说:“也许,真正的共感,并不需要高科技。它只需要一个人愿意停下脚步,对另一个人说一句??我在听。”
春天又至。
青海湖小学新一批孩子围在古井旁,老师指着水面问:“你们相信这口井真的能听见愿望吗?”
一个小女孩踮脚望去,忽然惊喜地叫起来:“我看见了!井里有座塔,还有铃在响!”
其他孩子凑上前,纷纷惊呼。
而在井水深处,倒影中的铜铃塔顶,十三枚铃铛轻轻晃动,仿佛回应着千千万万颗跳动的心。
风穿过树林,拂过草地,掠过湖面,带着一声极轻、极柔的叮??
飘向远方,飘进每一个愿意倾听的耳朵里。